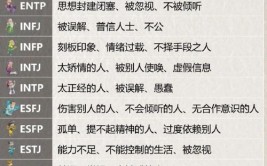[美]沃尔特·劳德着
如同一名参谋官日后所追忆的,发电机室内是一种“有秩序的混乱”,那么雄伟的峭壁成功向世人隐瞒了这项事实。多佛从未像五月二十六日这天那样明媚。海峡对岸传来隆隆的枪炮声——布洛涅失守,加来即将沦陷;但是对于安安稳稳停靠在唐斯(Downs)的船员来说,一切似乎非常遥远。
由明轮蒸汽船改造的“梅德韦女王号”扫雷舰(MedwayQueen),此刻停泊在峭壁边。大厨罗素倚在护栏上跟他的年轻助手闲话家常;罗素只知道他的助手绰号叫“赛克”。他们说道,很奇怪,今天早上整个船队都停在港内,没有一艘船出海扫雷。早餐后,一艘工作艇绕港一周,把每艘船的船长、大副和无线通信员接到旗舰上,大概是要打打官腔。这时,一艘海军驳船缓缓驶到“梅德韦女王号”旁边,送来一箱又一箱的食物,那是远超过船上四十八名船员塞得进肚子的分量。赛克评论道:“船上的食物足够喂饱一整支该死的部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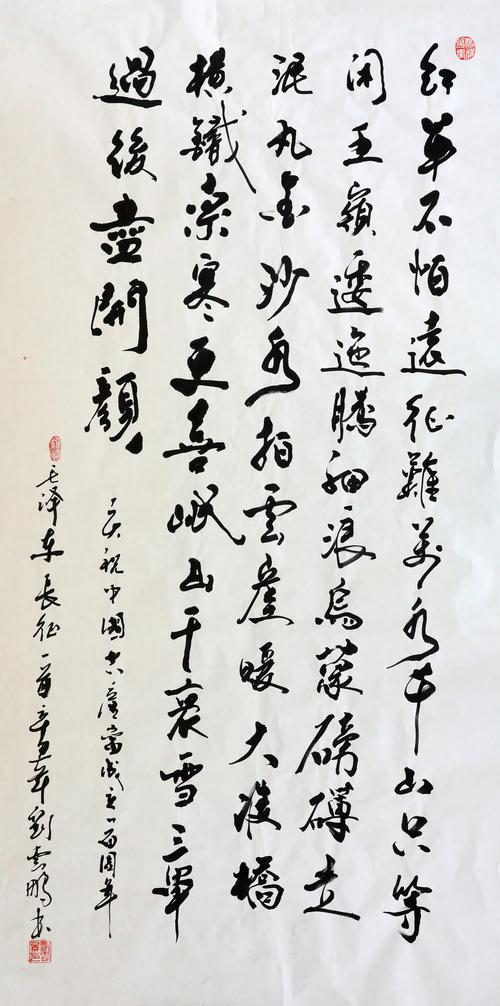
被围困在佛兰德斯的士兵,恐怕跟“梅德韦女王号”的船员一样不明就里。二十六日稍晚,来自第三军团总部的沃特金斯准将(G.D.Watkins)传给阿兹布鲁克附近的第四十四师指挥官奥斯本少将(E.A.Osborne)一份秘密简报。不过,军阶较低的士兵就只能倚靠流言了。第五十师随军牧师纽康姆有个在情报处工作的好朋友,他阴郁地暗示英国远征军预备朝海岸前进,上船回家——“前提是,德国佬没有捷足先登”。流言传到法伊夫及佛弗尔义勇兵团第一营:他们将退到海岸,上船出海,然后在南边重新登陆,从德军背后发动攻击。
当命令终于抵达,往往只能靠口耳相传。尤其是无所事事的皇家陆军补给与运输勤务队(Royal Army ServiceCorps),许多军官凭空消失。第四师弹药补给连的弟兄只被告知:“所有人自行想办法冲向敦刻尔克,祝大家好运!
”第一运兵连接到指示:“尽可能朝敦刻尔克前进,摧毁车辆,大家自求多福。”同样地,第五七三野战工兵中队也只听到老话一句:“所有人自行想办法前往敦刻尔克。”
命令通常毫无预警地抵达。在比利时的小村庄,天刚破晓,运输连上士史尼加尔就被口令声吵醒:“齐步走!
”他听见行进的脚步声,从他借宿的咖啡馆往窗外张望,看到他的小队正朝停车场行进。他赶紧追上,得知他们奉命砸烂部队的座车和摩托车,然后前往敦刻尔克。他们不可能搞错方向:只要朝远方的烟柱前进就好。
夜深之后比较困难。第二野战兵工场的洛克比中士开卡车摸索着往北的方向,直到一名军官跳到马路上拦下他的车,因为他正笔直朝五百码外的德军防线驶去。洛克比询问敦刻尔克的方向,军官指着低悬在地平线的星星说:“顺着那颗星就是了。”其他人则靠照亮夜空的炮火指引。此时,炮火几乎包围了四面八方,只除了北方的一小块缝隙依旧阒黑,那就是敦刻尔克。运输官希尔少校是握有地图的少数人之一。不过不是军方版——不知道为什么,战争一开始,后方地区的地图就被全数召回。他拿的是《每日电讯报》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战况而绘制的地图。
皇家炮兵第五中团的二等兵华克应该好好读读英法字典。他看到路标上写着“敦刻尔克”,纳闷是否就是他要去的敦刻尔克。 [1]
他不需要担心,只要留在走廊范围内——东界是比利时和英国的守军,西面由法军和英军防卫,最南端则是法军坚持死守的里尔——任何一条往北的路都行。
所有道路依旧塞满了井然有序或一团混乱的各式部队,从精神抖擞地手持步枪行进的威尔斯卫队,到类似四十四师炮兵连勤务兵佩吉这样的脱队士兵。佩吉在躲避机枪扫射时跟部队走散了,此刻正混在士兵和难民之中,孤独地往北跋涉。一辆硕大的比利时农用拖车从他身旁轰然驶过,上头载满了逃难的百姓,而佩吉意外看到坐在驾驶者旁边的竟是他自己的父亲。
“什么呀,这是我们的周日远足吗?”佩吉爬上车跟父亲短暂团聚时忍不住开玩笑。原来他的父亲——一名步兵营准尉——跟儿子一样迷茫。然后德国空军再度展开空袭,父子俩分开了……年轻的佩吉再次独自上路。“我们要去哪里?”他找人问路,得到老套的回答:“看见天空中的浓烟了吗?那就是敦刻尔克。朝那里前进!
”
远征队伍中也有女人,而且并非全都是寻常的难民。第二野战兵工场的法国联络官带着情妇同行,皇家运输勤务队的驾驶兵泰勒在里尔郊区发现一名在黑夜中啜泣的法国少女,因此想办法照顾她。他设法找到一辆军车,载着女孩出城,并且觉得自己颇有骑士精神——直到军车陷于车阵,他们下车步行之后,他失去了她的行踪。他从此再也没见到她,总是不由得纳闷自己的“保护”是否对她弊多于利。
东萨里军团第一营的二等兵贺塞运气比较好,他在图尔宽(Tourcoing)娶了法国咖啡馆的千金,事实证明,奥葛丝塔确实是个下定决心的新娘。当东萨里军团撤退到龙克(Roncq),她突然现身乞求贺塞带她一起走。在连长史密斯上尉默许之下,奥葛丝塔匆匆上了指挥部的卡车。
另一名战争新娘就没那么幸运了。当金妮·米榭在一九四〇年二月跟士官长高登·史坦利结婚,她成了第一个嫁给英国远征军成员的法国女孩。史坦利隶属于阿拉斯指挥总部的信号小队,金妮搬进他的宿舍,一直到五月以前,他们过着宛如和平时期的家庭生活。当“大战爆发”,他随着先遣队总部迁往比利时,她则回到邻近的塞尔万村,在妈妈开的小餐馆等待战争结束。
金妮对接下来两周的战事一无所知,所以当史坦利一天下午突然开着车顶上架了机关枪的指挥车出现,金妮吓了好大一跳。他告诉她,德军要来了,他们必须立刻离开。金妮急忙丢了几件东西进行李箱,外加妈妈塞给她的两瓶朗姆酒。一小时后,她准备好出门,打扮得就像要搭午后的火车进巴黎一样,身穿蓝色洋装、蓝色外套,并搭配蓝色宽边帽。
他们出发了,夫妻俩坐前座,一位名叫特利普的中士坐后座。马路上堵得水泄不通,更糟的是,金妮的宽边帽被风吹出了窗外。史坦利停车,当他往回捡帽子时,遭遇了第一次斯图卡轰炸。
子弹没打中,帽子得救了。史坦利继续向前开。他们头一晚在车上度过,其他晚上则多半躲在某个壕沟。有一次,他们睡在一名比利时农夫的大谷仓。农夫不答应借他们住,但史坦利拿枪射穿了谷仓门锁,一行人毫不客气地走进去歇息。
他们时而睡在干草堆里,时而跳进壕沟躲避斯图卡轰炸,全身上下越来越脏。金妮有一次想办法花十法郎买了一桶水,但是其他时候根本没机会梳洗。宽边帽早就支离破碎,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他们终于抵达一个叫巴约勒(Bailleul)的法国小镇,在一位老太太舒适的家落脚。容克里克夫人是个热情的主人,和他们在路上遇到的大多数人不同。他们隔天继续上路,斯图卡仍鬼魅般地缠着他们。
金妮这时已经完全走不动了,身上的衣服又破又烂。史坦利试着让她换上他的军服,再搭配钢盔,可惜没有一件合身。她终于告诉他事情是行不通的,她撑不下去了。他带她回到容克里克夫人的住处,老太太还是像以前一样热情好客,欢迎金妮留下来,一直住到马路畅通,她可以安全返回塞尔万为止。到了告别的时刻。史坦利是一名军人,有他应尽的责任,金妮完全理解。尽管如此,这一刻依旧叫人心碎。史坦利答应两个月后回来接她,这句承诺也只能稍微缓解痛苦。他会实践他的诺言——只除了“两个月”这部分,事实上,他最后花了五年时间。
金妮并非唯一一个濒临崩溃的人。负责带领第二野战工兵小队的年轻中尉屡次失去联系,终于忍不住流下眼泪。皇家运输勤务队的基奇纳中士发现自己陷在车阵中,拥塞的交通导致英国与比利时的驾驶兵打了起来。一名英国远征军军官试图劝架,结果被人推了一把,他掏出左轮开了一枪,射中基奇纳的左腿。“你射的是我,不是那个推你的王八蛋!
”基奇纳气炸了。
二等兵巴克斯是第十三战地救护车队随军牧师的驾驶勤务兵,他们的北上之路,变成一段由愤懑和互相指责构成的长征。巴克斯认为神父是个酒醉的懦夫,神父则指控巴克斯玩忽职守而且“愚蠢傲慢”。有好几次,神父自己开车扬长而去,留下巴克斯自谋生路。巴克斯也曾两度拿起步枪,仿佛打算用在神父身上。看来,就连上帝的信徒及其随从,也无法免于挫败的压力、接连不断的危险、饥饿与疲惫、炸弹、混乱,以及这趟走不完的撤退之路带来的烦闷。
二等兵史东尝遍了酸甜苦辣。他是皇家苏塞克斯兵团第五营的勃伦枪射击手。他们已经在走廊的东面连续作战两天,设法阻挡德军前进。此刻,他这一排弟兄奉命进行最后抵抗,让第五营其他人有时间撤退到后方重新整编。
他们坚守了一个钟头,然后跳上为他们准备好的卡车撤退。天已经黑了,他们决定找地方休息,毕竟他们已三个晚上没睡。他们在一栋建筑物前停车,发现那是一座修道院。身穿长袍的修道士从夜色中走出来,招呼他们随他进屋。
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穿着长袍和草鞋的修道士缓步而行,摇曳的烛光照亮了石头信道。一片祥和宁静,战争仿佛远在千年之外。院长表示很乐意提供吃住,给这些新来的访客以及另一群也发现了这处世外桃源的皇家工兵。
他们被引着走进回廊,在一张长桌旁坐定,每一名英兵都有一位修道士照顾他的一切需求。他们享用修道士自己制作的食物与美酒,吃了那么多天的饼干和牛肉罐头之后,这顿饭宛如皇家盛宴。
只有一件扫兴的事:工兵表示他们准备在隔天早上炸毁这一带的每一座桥梁,史东和他的弟兄必须在清晨五点前离开。而在饱经苦难之后,回廊的石头地板感觉就像羽毛床垫一样舒适。
他们于清晨上路。开车过桥的时候,他们小心翼翼减缓车速,以免触发已经埋好的爆破弹。这群皇家苏塞克斯兵团的弟兄走远了之后,远方传来了爆炸声响,这说明短暂的田园生活已经结束,他们又重回了战场。
除了炸毁桥梁、运河水闸、发电厂,以及其他可能对德军有用的设施,英国远征军也开始破坏他们自己的配备。对一名优秀的炮兵来说,破坏他多年来细心呵护的枪炮,简直是亵渎。当他们砸烂炮闩、破坏瞄准镜时,许多人当众哭了起来。
第三中团轰炸手阿瑟梅的痛苦甚至比其他人更深。他负责的是他父亲在一战期间使用的同一组榴弹炮,这被视为无上的光荣。炮身都一模一样,只除了现在使用的是橡皮轮胎,而不是古老的钢圈;战场也一模一样,远在这年春天以前,阿尔芒蒂耶尔和波珀灵厄早就是耳熟能详的地名。从许多角度而言,阿瑟梅觉得自己是在继承父业。
但是一战即便打得昏天暗地,也从未糟到要用炮管轰掉自己的炮台。他的良心倍受折磨,觉得自己“让老人家失望了”。
此刻,英国远征军正急着自我摧毁,没时间沉湎于这样的愁绪。在前往敦刻尔克途经的小镇上,例如翁斯科特(Hondschoote)及东卡佩勒(OostCappel),整支军队的装备消失在火焰中。好几千辆军车、半履带车、货车、重型卡车、摩托车、勃伦机枪运输车、野战餐车、小卡车以及指挥车在田野中排列成行,排光油料和水,任马达空转直到坏掉。堆得跟山一样高的毛毯、雨衣、鞋子、雨靴和各式各样的新制服被烧得精光。战地宪兵队的英厄姆下士经过一堆准备焚毁的衣物,他冲进去,扯开几捆包袱,找到合身的战衣,迅速更换,几分钟后重新归队——“是一票弟兄当中唯一衣冠楚楚的家伙”。
三军合作社的商店也是英国远征军的物质享受来源,根本无人看管,任君取用。轰炸手阿瑟梅往旅行袋里塞了一万根香烟,大摇大摆地走出商店。
随军牧师也加入了疯狂的破坏行动。第五十师的纽康姆牧师忙着砸毁打字机和油印机,他的办事员则负责破坏连队的电影放映机。后来,纽康姆也烧掉了两箱祈祷书。那是五月二十六日周日,不过这天不会有礼拜仪式。
北方二十英里外,笼罩在敦刻尔克上空的浓烟并非出自英国远征军的毁灭行动,戈林正设法实现德国空军独力赢得胜利的诺言。将近一周以来,凯瑟林将军率领第二航空队的亨克尔、道尼尔及斯图卡不断轰炸这座城镇。一开始,空袭造成的损失很零星,不过在五月二十五日当天,一场全面轰炸损毁了主要的港口水闸、切断了一切电力来源,港口受到严重破坏,一整片起重机吊臂倾斜成疯狂的角度。
四十二岁的雅克雷中士隶属于兵工队,他正跟其他“米虫”一起等待撤退。这时,他的小队被紧急召去,徒手替一艘弹药船卸货。起重机坏掉了,而平常在码头的装卸工人全都跑得不见人影。
接近中午时分,雅克雷的心思开始飘到其他事情上。敌军的飞机暂时离去,他注意到附近有几间引人注目的仓库。他熘了过去,发现了几个似乎特别诱人的大纸箱。他打开一个纸箱,可惜里面不是手表、相机之类的东西,而是满满的棉花糖。
为了物尽其用,雅克雷拿了一箱棉花糖回到码头,立刻大受欢迎。他回到仓库多拿了一些棉花糖,又找到了一大桶红酒。他装满水壶,开始品尝。他再一次想起自己的弟兄,也带了些酒回去给他们。这群人喝得太开心了,他又回去多拿了一些。直到天黑以前,船上的弹药卸了不到一半。
隔天(二十六日),这群人回去工作,雅克雷的眼睛再度四处打转,这一次,他找到了一辆满载内衣裤的货车。他继续搜寻,在另一辆车上找到尺寸刚好的鞋子。他再度跟朋友分享好运,码头的工作也再度停摆。那天夜里,船只在货物没有卸完的情况下回到海上。
敦刻尔克
[美]沃尔特·劳德着
敦刻尔克1:甘末林误判局势,法国军团主一下子就被打得溃不成军
敦刻尔克2:德国已派遣出多名打扮成修女、神职人员和学生的间谍
敦刻尔克3:部队被切断补给,士兵们迷失方向或被完全遗忘在大街
敦刻尔克4:法国第一军团溃不成军;伦敦巴黎继续做美梦策划反击
敦刻尔克5:丘吉尔认为只能救出两万到三万名士兵,他押注十七号
敦刻尔克6:德国国防军耽误了整整三天,丘吉尔侥幸且意外的收获
敦刻尔克7:调派海峡邮船、观光船、商船、渔船、救生艇、游艇
敦刻尔克8:海军总部在五月二十二日将撤退计划定名为发电机行动
敦刻尔克9:所有人自行想办法前往敦刻尔克,朝远方烟柱前进就好
敦刻尔克10:首相决定死守加来,战到最后一兵一卒,拖延德军前进
敦刻尔克11:德国装甲部队击破英军侧翼,炮兵连和德军间毫无屏障
敦刻尔克12:喀麦隆高地兵团,最后在战斗中穿百褶裙的苏格兰部队
敦刻尔克13:没足够的船,盟军佛兰德斯争取的时间,都将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