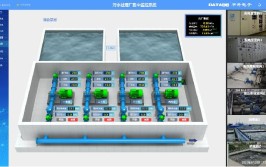新安江中浅水时必须拉纤
险滩激流中的船只
比拉纤还苦的撑夫

生 活 篇
桥,说白了就是连接南北,交易东西,方便生活。“修桥铺路”就是古代德政和仁政的代表政绩,也是证明资本家是不是“慈善家”和“大善人”的重要指标。要知道歙县南乡人为什么这么高兴,先要了解一下以前百姓的出行。
歙县昌溪木板桥
歙县,作为古徽州的一部分,坐落于群山之间,注定了“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命运,作为当时“丢出去”最为便捷的方式之一就是坐船沿新安江顺流而下直奔钱塘,到达余杭,转辗全国,开拓徽州人的星辰大海。
不过对于生活在新安江边与浙江交界的居民来说就有点尴尬了,因为“诗和远方”可以坐船去,“柴米油盐”、“走亲访友”也必须坐船去,哪怕就能看见,还能喊话打招呼,你就是过不去,由于各种原因,家在左岸,田地在右岸的情况也非常多。一条新安江化作一条白蛇巨蟒,阻隔两岸,于是有了“深渡、小川渡、街口渡”,便宜实惠,也能过河,不过有点废腿,也耽误工夫,因为渡船虽然是解决了过河的事情,但是还有很多路要走啊,还有东西要背啊,遇上那种卡在两个渡口中间的地方,走路都要半天。
歙县深渡大桥
要是出门就能过河岂不美哉,虽说有蚱蜢小舟不受渡口限制,但是以前普通百姓也搞不起啊,小船再小,也是很大的固定资产,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共享单舟”,要想过河要么迈腿绕路,要么搭“顺风船”,要么体能好自己游过去,新安江蓄水前赶上枯水期,卷起裤管趟水过河也是可以的,至于危险肯定是有的,一切看运气。
划船过河能有什么危险呢?
“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
“深潭与浅滩,万转出新安。人远禽鱼净,山深水木寒。”
这些古人诗句都告诉我们了,新安江落差大,水流急,浅滩多,深潭密,这些都是一个一个的盲盒,危险就来自于遇到这些盲盒一般的“深潭与浅滩”,当地人熟悉水文会好点吧!
会好一点,但是新安江流速快,“明天和意外”总是不规律出现的。深潭与浅滩
当然除了看运气,也要看天气,稍微刮个风,都不要过河了,河道内的风可是猛地很。
到了近现代,可算是好了,在1934年间,屯淳公路开通了,可以直接坐车到屯溪或者淳安转车了。不过,江那边的人怎么办?要是有桥该多好啊!
大概就是从这时候起,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就有了这么一个念头,这新安江上要是有桥该多好了啊!沿岸百姓,操舟往来
后来建设了新安江水库,公路被淹了,河面变宽了,虽然船只多了,过河方便了,但“有桥多好啊”的念头一直根植在大家的大脑里,于是先后出现了不少大桥,深渡大桥、小川大桥、新溪口大桥、塔坑大桥、街口一桥(暂且这么称呼吧),有点可惜的是这些桥都不在新安江的主干上,全部在新安江主干和支流的交汇处,但是这些附近的百姓是受益的。
其实 “桥”这种设施和以前的“渡”其实也是一样的,总不能家家门口建一座桥吧,这肯定不现实啊!
好在新安江两岸先后有了公路,有了公路总该方便许多了吧!
恰恰相反啊!
有了公路,虽然有些地方出远门会绕路,但真的是方便了,不过两岸往来反而更加不便了,原因很简单啊,有了公路,船自然就少了,顺风船就自然而然更少了,要想过河只能自备小船,于是连住在高山上的人家基本也是过上了“有车有舟”的日子。风和日丽的时候是一种惬意生活,但是……
小船多了,自然危险也多了,遇上刮风下雨、雾锁新安的时候,两岸往来就全部停止,正是应了那句“来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
要不说人的要求总是不断的提高呢,这时候的歙县南乡左岸是一套交通系统,右岸也是一套交通系统,但是不能联动,这和习武之人不能打通任督二脉一样,于是乎在新安江上修大桥的愿望达到了顶点。
街口滩头村成为沿江最后通车的地方
现在终于明白了以前有个词叫“路桥”,先有路再有桥,两岸公路都修好了,桥就是打通任督二脉的关键,于是安徽境内新安江上终于要修第一座大桥了,你说大家能不关注吗?能不开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