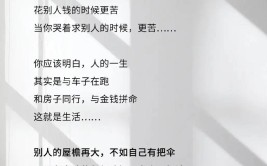◈ | 连亭
一直以为,是树把天上的灵气输送到地面。作为连接大地与天空的桥梁,树勤恳地充当大地与天空的使者。即使在大城里树与树的联系已经被我们阻断,无法连成森林。
大城有高楼、豪车、公路、霓虹灯、商场,有吃喝拉撒、喜怒哀乐。熙熙攘攘,纷纷扰扰,名利场中手起刀落,光怪陆离中万金如土。芸芸众生,众生芸芸,左不过是生老病死四个字。

生、老、病、死,是大城也不可避免的命题。再坚固的水泥,也终将老化。再高大的楼房,也躲不开风雨。再先进的科技与医疗,大城里的人也逃不开生老病死。这四个字,仿佛轮回的魔咒,谁也免不了,连死物如土石的大城也不能。不仅如此,这四个字占全已是大幸,而有的只得其中之“生”“死”,而无“老”“病”之机会,襁褓之中则夭折;而能够“生”“老”“死”而无“病”的,似乎从来没有。这四个字,只一个“生”字稍带喜庆,“老”“病”“死”与人如影随形,也与城如影随形。
因而,人们还想在大城保留一些持续的东西,比如泥土,比如在泥土上种一些树。这些树,是他们从城外强行搬进来的,由于水土不服总有些营养不良,但毕竟算得上是树。大城有了树,仿佛装了无数鲜活的净化器,人们在呼吸中,也仿佛觉到了光合作用的律动。
没有树的城市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没有鸟停歇的树是悲哀的。我一向不喜欢缺乏绿化的城市,霓虹闪耀、车水马龙的繁华热闹,若是没有树作为衬托,也只是没有生气的热闹而已。堆满楼、车的大城是死的,而树的加入,激活了城市。树静止时,如大城恪尽职守的卫兵。树摇动时,荡漾出轻微的波浪般的乐声。在树的一静一动中,大城获得庄重和脉动。而这庄重与脉动的布景里,常常少不了鸟的身影。在大自然中,鸟是跟随树生活的,人们把树搬到大城,就把鸟引来了大城。唧唧啾啾的鸟声,给大城增添一抹轻灵的亮色。
树本来长在乡野,由于人之关系,移进了大城。大城里的树,或许是旧的结束,或许是新的开始。冥冥之中,似乎是注定。或许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瞬间,比如树变换了风的走向,比如树接住了病房窗前的一缕目光,比如树读懂了匆匆行人的疲累,一切就有了不同的未来。树的每一次摇动,每一次呼吸,不经意间已将大城悄然逆转。于是,水泥砖瓦不再冰冷,生老病死不再艰难。
一直以为,是树把天上的灵气输送到地面。作为连接大地与天空的桥梁,树勤恳地充当大地与天空的使者。即使在大城里树与树的联系已经被我们阻断,无法连成森林。
在大城,人是容易忽略深受其裨益的树和鸟的。这是因为,树没有楼高,鸟鸣时声音也容易被汽车的噪声淹没。在大城,似乎人与树,各有各的存在,人和鸟,各有各的活法,可较之于人,大城更亲近树和鸟。树是大城的佛性,鸟是大城的神性。
鸟类一出世,就具有俯视人类的高度。在漫长的日子里,它们始终在比人高的树上歌唱、捉虫、睡觉、孵蛋,我们从来都只是仰望,而很少去惊扰,与其说是因为鸟,不如说是因为树。树拉开了鸟与人的距离,就隔开了一个缓冲的安全地带。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与鸟之间没有关联,在相安无事的岁月,人总会在不经意间为鸟而激动,比如有时经过一棵树,听到鸟鸣周匝,我们的耳朵会突然醒来,我们的头会不自觉地抬起来,对鸟投以欣喜的目光,对树发出由衷的赞叹,我们混沌的兴致一下子活过来,突然哼出一些遥远的曲调,仿佛自己又变回那个新鲜的血肉丰满的人。
我时常对大城里的树投以惊叹的目光,虽然它们脚下的泥土那么少,但它们的枝叶依然繁茂,始终朝着天空和阳光的方向延伸。走在大街上,坐在公交车上,站在窗前,我总在凝视所见到的一棵棵树,树也同样以宽容和悲悯的目光注视我。
我发现,不管人们在不在意,他们越来越离不开树了。在家里睡眠和在写字楼办公,他们需要树吸音;在公园与河边晨练,他们需要树来辅助吐纳;在车站候车,他们需要行道树来站岗和维持秩序……
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们的寿命与树有关联。他们以树喻长寿,好像是树使得沉重的生命有了依傍。越是上了年纪的人,越是着急往树奔去。每当清晨和傍晚,社区里的大爷大妈,都郑重其事地从家里出来,走到公园里,走到广场上,走到任何空旷的地方,专心而虔诚地抱着一棵树练习吐纳。
前阵子我的一个朋友在大城添新居,费尽心力地将老家的一棵月桂搬进新家的花圃。我去看了这棵月桂,它已经有腿胳膊那么粗了。朋友说,这棵树是断不能割舍的,倘若不能将它带来,宁可回老家也不进城。这话未免夸张,却具备心理的真实。我想起作家苏童也曾为“三棵树”耿耿于怀过。从小为没有属于自己的树抱憾的苏童,1998年突然在城里拥有了两棵树。苏童在《三棵树》的文章里说,这两棵树弥合了他与整个世界的裂痕,让他确认自己是幸运的,这是父母和朋友都不曾做到的。
我曾在医院,倾听将近一个月的树声。那时我生的病,不是什么大病,却得住院,得手术,手术后又得住在白惨惨的病房里,年纪轻轻的人怎么受得了呢。况且,又不能看书,不能见很多的人,一天到晚或躺着,或靠着,无聊得很。我多么希望能跟外界多一些交流啊,只要能够冲破狭小的病房,什么都是好的。闭上眼睛祈祷,我听到了一棵树的声音,沙沙沙,沙沙沙……我还听到了鸟儿的声音,唧唧啾啾,唧唧啾啾……我睁开眼睛向窗子看去,见不到树,偶尔能看到鸟儿掠过窗玻璃的身影。我想,那窗子底下必定是站立着一棵树的,不然哪来的沙沙沙声与鸟儿的歌声呢?我问从外面回来的母亲,母亲说:“是呢,是一棵碗口粗的杉树。”等我能从病床上起来走动时,就时常到住院楼下的院子里,看那棵杉树。它挺拔、秀丽,竟还隐藏着一个鸟窝,我猜想那里边一定卧着雪白的鸟蛋。呵,一棵医院的树上,生命正在悄悄地孕育萌发!
一个清晨,我在病房里醒来,听到沙沙沙的树叶声中,夹杂着雏鸟的欢叫声,急忙下楼去看,只见鸟妈妈正给小东西喂食呢!
医生说,我心态好,对治疗积极配合,手术后恢复特别快,可以提前出院了。我竟有点舍不得那棵住着鸟儿的树。呵,我幡然醒悟,我的康复是它们赐予的呢!
从医院出来,我又走在大街上,走在一棵棵树之间,树还是那么生长着,大城还是那么繁闹着,似乎毫无变化,亘古永恒,又似乎不管我离开多久,它们依然在此等待啊——
一天深夜,我加完班走到一株泡桐树下等末班车,昏黄的灯光照着我,也照着树。莫名地,眼前这一片月色般的灯光在内心浮泛开来,回望来时的寂静大街,那一棵棵挺立在大城的树,好似一个一个的人。
END-
喜欢的点个【在看】,当你读完这篇文章时,希望你可以将它传扬出去,传播一些积极正面的信息,让世间多一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