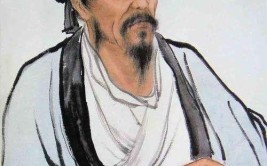文|王智才
有一年的春节大年初三,天色阴沉,北风萧萧。下午,父亲要我陪他去兴化“银北门”转转。
天气阴冷,行人也稀少,但我们兴致丝毫不减。一路上,两边的“槅扇”门,只是紧闭,好些早已破旧不堪,连对联都
“银北门”又叫兴化北城门外大街,顾名思义,这条大街地处城外,直通向兴化城北门。每逢春节间,父亲常到这一带转转。这习惯已有多年。父亲曾说,这里留下他童年美好的回忆。据他回忆,小时候曾无数次随他父亲到这儿卖鸭蛋、鸭子、鸡子,同时又往往买回好多的家什用物。对一些店铺主人的姓名、性格、身世,甚至街巷里弄的一些人物掌故等,他耳熟能详。在他那富有感染力地描绘下,一些人的形象,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栩栩如生。

过去乡下有句俗语:三世修不到个城脚根。就是说,农村人想成为城里人,哪怕仅寄居在城墙脚下,也几不可能。许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我小时候对兴化城无限向往。其实,我们村庄离兴化城也就十里左右。但那时上兴化一般靠步行,去一趟也不容易。一旦得知父母明天要带我上街(我们过去把上兴化城叫“上街”),这夜兴奋至极。黎明时分,在鸡啼前就已醒来。匆匆吃了早餐,就跟父亲“上街”了。
走过几个村庄,就能看到远处的兴化城。烟囱、水塔、无线电塔、大楼,似乎在朝我招手。蜿蜒的兴盐公路如一条光带。越走越近,喧嚣声似乎隐约可闻。这一切都会激起精神亢奋,繁华世界居然近在咫尺。
小时候,对兴化城印象最深的,是那逶迤弯曲、如迷宫一般的、小青砖侧铺的“银北门”街巷。一踏上青砖,就让人切实感到已身置兴化城里了。街巷两边,店铺几乎挨家挨户。安插在上下的木质轨槽里的一扇扇木板(即“槅扇”),算作店门。早上营业,将木板抽去;晚上打烊,再将木板依次插上。木板使用有些年头了,某些部位显得那么光滑。这边是无线电修理部,那边是钟表修理店,再前面是一家布店。这些布店的结账方式很特别。会计坐在一个高台上,前面有一些铁丝,每根铁丝都与各柜台连接,每一根铁丝都穿着一个铁夹,人们叫做“梭子”。若要给顾客找零钱,店员就将人民币和发票夹在“梭子”上,“嗖”的一声,“梭”向会计处。会计算完账,将发票及应找的零钱夹在“梭子”上,“梭”向柜台处。至今回想,一切都历历在目。
俗话说:大人贪利,孩子贪嘴。小时候和大人上街一次,总免不了垂涎于各种吃食,眼睛总要溜向两边的吃食小摊。街巷两边常有炸麻团油条的,水果摊各色水果水灵灵的整齐地排放着,引人垂涎。而我最想逗留之处的是混沌店,因为那里有我最爱吃的肉包子。老远就能听到“呜呜”声响,那是鼓风机吹着火炉的声音,火炉上的笼子正蒸着肉包。蒸汽腾腾,肉香四溢,让人口舌生津。我望见里面穿着白色护身衣的员工,端着热腾腾的一笼笼的包子,曾立下宏伟志愿,长大一定要做蒸包子的人。还有酱品店、散酒店、衣帽鞋袜店等等林立两旁。更有小商贩,推着板车沿街叫卖的吆喝声,来回穿梭的自行车发出的铃铛声。“叮铃铃,叮铃铃”一阵急促的铃声,提示你赶紧闪开。“银北门”给人记忆是永远是鲜活的、繁华的。
然而,不知从何时始,“银北门”逐渐萧条黯然下去。记得10多年前,这里已不似往昔之繁华。行人稀少,很多店面已变为纯粹的住宅,里面也大多住着些老年人。昔日的喧腾已变得渺远起来。是的,不远处宽阔的大街,两边林立的高楼,大型集市、超市,早已将“银北门”挤出了九霄云外,淡出人们的视野。它犹如人的一生,经历青壮年的血液贲张,而今已是迟暮之年,安详宁静,幽居一隅。它曾经的繁荣,也只能留在我们及父辈那一代人的记忆深处。现代有多少年轻人,愿意踏上这块青砖小巷,站在苔痕布满的青石板上,作幽眇的追怀?是的,谁愿意和一位沧桑的老人亲近呢?
然而,“银北门”的繁华盛世,并未从我们这一代的记忆中抹去。随着岁月的流逝,反而愈加对它有怀念之意。说实话,它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梦境中,一切无比清晰地呈现儿时的模样。每每醒来,唏嘘不已,辗转难眠。
我和父亲沿着北大街继续向南,迎面就是北水关新建的仿古式城楼了。我说,从前的城门是不是这样子。父亲笑着摇头,首先是方位错了,过去的城墙应为东西走向,城门朝北。现在这样建造,可能是受建筑场地所限。我这才注意到,如果东西方向建造,固然更能保持原貌,但将会遮蔽背面相当一部分住户的阳光。我好奇地问,兴化还有古城墙吗?父亲笑着没说什么,只是要我跟着他继续向前。越过一条马路,穿过一个小区,经过一道小巷。沿巷向前没多远,又拐向西十多米,忽见一堵青黑色的墙壁。父亲说,这就是古城墙,据说为唐程咬金建。我心微微一动。走近它,南北约二三十米,高约五六米。每块城砖约有普通砖块的三四倍大。墙面斑驳,苔痕布满。一些小草从砖缝中滋长,风吹来,萧萧瑟瑟。我用手触摸它粗糙的墙面,感到时间瞬间凝固,历史就在眼前,它正在向我倾诉千年悠韵。只可惜,我对它浅薄苍白,竟无可共语。在这堵厚重的古墙前,我顿感人的渺小。
回来路上,我就想,父亲是一个乡下农民,何以对兴化城如此熟知?除了他童年跟他的父母经常来做买卖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在回家的路上,父亲不像来时的谈兴,沉默许多。走着走着,他突然口占一绝,具体内容我已忘了,大致是关于我们这次游玩的经历。我突然想到,父亲虽是农民,但爱好文史。只上小学四年级的他,两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上下集),早被他翻得边角异常粗糙。《阅唐》《岳飞传》等民间俗本,也被他翻得棱角磨损。我突然找到了答案。父亲对兴化城历史如此的熟悉,尤其对“银北门”如数家珍,无非是一看二听所得。若没有对历史文学的兴致,谁会留心于那些古宅旧楼,残垣断壁,感兴于那些途说道听呢?
我很幸运,有这样一位爱好文史的父亲。在他所谓的熏染下,我从小就保留一星半点的古文化爱好的因子,并能绵泽至今。此时在这个寒峭下午,古道深巷处,迎来了一对父子。他们时而漫谈细说,有时驻足指点凝望。他们徘徊在这片古风悠悠的青砖黛瓦间,沉浸在历史的韵味中,久久流连不去……
作者简介:王智才,江苏省兴化市板桥初级中学。
投稿邮箱:huanghaisanwen@163.com
壹点号胶东散文
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全省600位在线等你来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