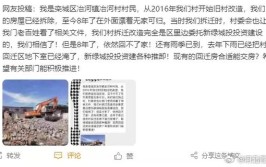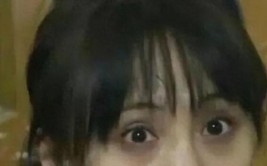所以,它们没有马上远离,没有立即高飞,而是轻展双翅,从田埂上落在了水田里,而后移动脚步,用长喙找寻食物——好心的村民头天晚上知道小家伙要来,买来了泥鳅、小鱼,倒入田中……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有白鹳飞过,阵阵鸟声从远处传来。小家伙们开始不约而同收喙驻足,并向着同一个方向侧耳倾听——它们在接受并试图破译大自然的密码,尽快加入鸟类的大家庭。
这里,是万年县梓埠镇,这3只东方白鹳的出生地。这一刻,是放飞它们的“黄金时间”——2020年6月17日10时。

15时,小家伙们终于走近其他白鹳,随同类觅食、飞翔……
6月16日 饯行
晨曦映在南昌梅岭上,白云变幻,蓝天如洗。轻风掠过,景色撩人。
梅岭脚下,公路铁路在这里交会,路边分布着零星的菜园、小水塘、水沟。6时许,一胖一瘦两个小伙子穿着高筒套鞋,出现在水沟边。
胖高个提着塑料桶,深一脚、浅一脚跟在瘦小伙身后。瘦小伙拿着一根长竿子,竿子末端接个小渔网。他把渔网往水草里一探、一提,就有小鱼、小虾或泥鳅落网。他随手把鱼虾甩到水沟边的草丛中,胖高个立即捡起来,放进桶里。动作娴熟,配合默契。
转眼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小鱼小虾装了小半桶。
阳光照在了他俩身上,胖高个满头冒汗,瘦小伙衣服也已湿透。
瘦小伙看了看,对胖高个说:“再去捞一点。怕不够它们吃。”
它们,是养在省林科院野生动植物救护繁育中心里的3只东方白鹳。
说这话的小伙叫况绍祥,胖高个叫孟璞岩,都是中心的执业兽医师。小况在梅岭脚下长大,从小喜欢摸鱼捞虾,哪里有“野塘”“野沟”,他一清二楚。
将近1小时过去了,桶里的鱼虾越来越多。看看差不多了,他俩收拾好家伙,提上鱼桶,各骑一辆电动车来到中心。
中心面积不大,是市郊难得的一块僻静之地。长住这里的饲养员徐美号接过鱼桶,走过一段碎石子路,进入一个院子,院子一半盖瓦、一半露天。网格“房间”里,3只白鹳站在人工搭建的窝棚上。老徐打开“房门”,将鱼倒入池中。
3只白鹳从巢里跳下来,步入池中,享受着新鲜美味的早餐。
站在远处的小况和小孟,默默看着这3只小天使。良久。
院子一角,立着3个1米多高的木箱,箱子四壁都预留了一个个用于透气的小孔。
过了今晚,这些大木箱将派上用场——装上这3只白鹳,运至它们的出生地,让它们回到鄱阳湖的怀抱——那是它们永久的巢。
3月30日 发现
两个多月前的江南,树木长出新叶,水田正在翻耕。万年县梓埠镇一边靠高速公路,一边倚乐安河。万顷良田里,点缀着村庄、鱼塘、荷池。一座座高压线铁塔矗立在农田里、村落边。电线从塔上穿过,穿过江面、穿过田畴,向两头延伸。
这条高压线,是500千伏南乐线(南昌至乐平)。全线有铁塔611座,每座铁塔高达40米左右。
36岁的刘璐,是这条高压线上的“卫士”——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输电运检中心输电检修一班员工。
3月底,他和同事巡线时,发现梓埠镇一座铁塔上,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凭经验,他断定是白鹳筑的“特大型鸟巢”。在这条线上工作10多年,他什么鸟都见过。靠着公路、河湖,傍着树林、人烟,闹中取静,食物无忧。“据我观察,白鹳的鸟巢有一米厚,平面有八仙桌那么大。白鹳是搭巢高手,一般一个月就可以在铁塔上建一个鸟巢。我们开玩笑说,它比建筑工人还厉害!
”刘璐说。
30日下午,副班长别会春操作无人机检查。一看,果真是白鹳。再一看,有只大鸟站在鸟巢里,警觉地张望,另一只大鸟则一动不动地趴着,旁边还呆着几只小鸟。
“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们不能随便动它。”31日,班长杨志广辗转联系到万年县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站长张丽君,告知这一情况,并请求支援,一起为白鹳和电路做安全防护措施。
当天晚上,班组回到南昌大本营。“大鸟跟母鸡一样,趴在那里,难道真是在孵蛋吗?”刘璐表示怀疑。他们把无人机拍的视频下载到电脑上,放大仔细看。这一看,惊住了。
“有一只大鸟的头耷着,翅膀垮垮的,身上有很多污点,可能是小鸟拉的鸟粪吧。”刘璐回忆,“难道大鸟已经死了?”
刘璐不是第一次在铁塔上发现白鹳。“一般来说,孵幼鸟的白鹳,一般有一公一母,一只护巢,一只找食。两只大鸟同时呆在巢里,而且一只一动也不动,肯定出了状况。”
4月1日白天 营救
这天上午,杨志广再次拨通张丽君的电话。张丽君一听,马上通报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万年保护监测站。她请杨志广班组去现场协助他们。杨志广二话没说,带着刘璐、张涛,从南昌赶往梓埠。
一场营救展开了。
白鹳是冬候鸟,一般不在江西繁殖;之前省野生动植物救护繁育中心也救护过白鹳,但救护在江西出生的白鹳幼鸟,中心没有先例;对万年县来说,更是第一次。
“林业部门的人说大鸟不行了,要我们配合,把它搬下来。”刘璐说。当时疫情较重,还处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状态,刘璐和张涛爬上铁塔之前,穿好屏蔽服,戴好口罩和硅胶手套,带着绝缘绳、袋子等,向铁塔顶端爬去。
“当时线路是在运行状态,电线带电,我们既要保证自身安全,又要保护鸟的安全和电路安全。”刘璐说,他们往上爬的过程中,守护鸟巢的大鸟突然腾空而起,围绕着他们,在铁塔上空盘旋良久,最终落在另一座铁塔上,看着他们。
花了近20分钟,刘璐、张涛爬上了铁塔顶部,并慢慢靠近鸟巢。腐臭味向他们袭来。巢里的那只大鸟已经死了。张涛慢慢把死鸟抱起,装入袋中,再用绝缘绳将袋子缓缓放下,直至地面。
那只飞离的大鸟,又开始在空中盘旋。
整个清理过程花了40多分钟。事后张丽君赶往县城;杨志广班组则前往下一个工作点。途中,刘璐和张涛仔细回想刚才在巢边看到的一幕:好像那3只小鸟都是耷拉着头的,只有个头稍大的那只小鸟,头偶尔会动一下。
“估计那3只小鸟也快不行了。”刘璐说。
杨志广一听,又拨通了张丽君的电话。
张丽君也懵了。她联系同事汪辰。小汪在大学一年级就跟着老师做候鸟保护的课题,听说一只亲鸟已经死亡,心里一紧,又听说还有3只幼鸟也无精打采的,心里更急了。
“如果状态好的话,3只小鸟食量是很大的。一只亲鸟肯定养活不了它们。”汪辰告诉张丽君,如果小鸟没有精神,说明食物没接上。
这些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小汪拨通了他老师的电话。老师说:“赶紧把小鸟送省林科院野生动植物救护繁育中心,不然它们过不了今夜!
”
张丽君再次求助杨志广:“杨班长,辛苦你们回到刚才那里,我现在从县城往梓埠赶,必须把那3只幼鸟救下来!
”
下午,他们第二次在铁塔下见面。
还是刘璐和张涛两人上铁塔。这次,他们带上了一个硕大的绝缘桶。
“这个绝缘桶可以保护小鸟在桶里不跑出来,不会触电。”刘璐说。
他们靠近鸟巢,张涛把绝缘桶绑定在身上。刘璐向巢里伸出手,那只个头稍大的小鸟突然啄他。“叨的一下!
还好我戴了绝缘手套。”刘璐说。
刘璐小心翼翼地将3只小鸟放入绝缘桶,张涛在桶口打上特殊的结,使绳子完全扣住桶口,确保小鸟绝对安全。
刘璐发现,在他们的头顶上方,那只大鸟仍在不断盘旋……
4月1日晚 急诊
张丽君、杨志广第二次赶往鸟巢时,另一场战斗已在省林科院野生动植物救护繁育中心打响。
这天下午,况绍祥在省林科院一个微信群里,看到大家在热烈聊着这几只白鹳——
“东方白鹳是在北方繁殖的,南方一般都在高压线铁塔上繁殖。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护得好。”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濒危物种吧?不足4000只了。”
“不是有成鸟在边上嘛?成鸟不去觅食喂养吗?一般不建议人为救助。全带走的话,太惨了,妻离子散。”
“也有配偶死亡,成鸟再也不离窝的。”
…………
况绍祥赶紧在群里说:“先送过来看吧。”
他放下手上的活儿,叫上孟璞岩:“走,我们赶紧捞点鱼虾,晚上有3只小白鹳要来。”
在“野塘”“野沟”捞鱼虾时,小况还不忘叮嘱送白鹳来南昌的张丽君:“麻烦告诉司机,开车慢一点,不要急转弯,也不要急踩刹车。”当时天气湿冷,他不忘补充一句:“如果能开空调保暖就更好了。”接着发了一张照片——一盆刚捞到的小鱼小虾,“小白鹳的食物准备好了。”
中心主任汪志如说:“万年那边把死了的大鸟也一起带了过来,我们对它解剖,发现有卵巢,说明这是只雌鸟,是3只幼鸟的母亲。”
中心接到3只幼鸟时,是晚上9:30。之前中心救助过的小鸟,只要没有大问题,正常喂食,小鸟都会主动吃。这3只幼鸟,个头大点的,精神稍好些,但也不会主动进食;另两只几乎都不动了。
小况只好强行给它们喂食。中等个头的,生命体征更弱,喂食不多久便拉稀。小况赶紧给它输液,直到次日,这只小鸟才勉强有了一点精神。
这边输液、喂食,那边为幼鸟搭窝,增添保暖设施,中心的工作人员一直忙到半夜。
“那几天,我最发愁的就是为白鹳找吃的。总不能天天让小况他们去找鱼吧?”2日凌晨,汪志如天没亮就开着车子,到赣江边的水产市场。市场虽大,却买不到一寸大小的鱼。“这么小的白鹳,几天没吃,身体虚弱,又有病,鱼虾稍微大一点,就吃不下。”他说,亲鸟一般是把觅来的食物在自己的嘴里嚼烂了以后,再送进幼鸟嘴里。“真是多亏了小况他们。”
那几天,小况和小孟一天两次到梅岭脚下的“野塘”“野沟”捕鱼捞虾。“没想到我小时候练就一身捞鱼捞虾的本领,今天会派上用场。”小况有些沾沾自喜。
小孟记下了那几天的情况——
4月1日,晚上,送达中心,中等个拉稀、输液,人工饲喂鱼;
4月2日,保温,人工饲喂,中等个拉稀、输液。
4月3日,保温,自主进食,中等个恢复正常;
…………
5月20日 “越狱”
看到3只小白鹳身体恢复健康,渐渐长大,汪志如心宽了许多。这天一早,他就带着小况和小孟,离开南昌做野外调查去了。留下职工黄秒根和饲养员徐美号看护鸟儿们。
12时许,吃过中饭的老徐走向饲养白鹳的小院,那里除了3只小白鹳,以及被救护的天鹅等野生动物外,角落上还有一间房,那是老徐的房间。
还没进院子呢,老徐看见不远处有两只鸟。“那不是白鹳吗?”老徐汗毛都竖起来了,蹑手蹑脚走近白鹳。白鹳见了老徐,也不躲避。老徐张开双手,轻轻扬动,把两只白鹳往院子里赶。
白鹳竟然很听话,进了院子,走进它们的“房间”。
可是,那只个头稍大的白鹳不见了!
老徐吓得大气不敢出一声。他把两只白鹳赶进“房间”,跑出院子,跑到中心门口右侧平房里,猛敲黄秒根的房门。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老黄正想午睡,听到老徐在门外喊,“一只白鹳不见了!
”
老黄也吓得不轻,来到院子里查看究竟。确定少了一只白鹳,他什么话也没说,和老徐两人跑出中心大门找白鹳。
走了这条街,没看到白鹳的影子;扫了那条路,也没新发现;不远处的梅岭,不见鸟儿飞过,哪怕是活动的白点,一个也没有。他们见人就问,甚至拦车打听。一名撑着伞的女子对他们说,她看到了有只很大的白鸟飞过,还用手机拍了照片。老黄赶紧把照片发给汪志如。汪志如说:“继续找,直到找到为止!
”
在街上找了4个多小时,夜幕逐渐落下。两人拖着酸痛的腿,回到了中心。
正当他们垂头丧气时,眼尖的老徐突然叫了起来:“那只鸟!
”
老黄循声望去,中心附近一幢高楼上,正站着那只白鹳!
它望着中心,一动也不动。
汪志如看到从微信里传给他的照片,喜出望外,继续遥控指挥——
老徐每隔两小时,必须看看楼顶上的白鹳在不在;老黄在老徐的房间里蹲守,准备一根长绳子,一头系在白鹳的“房门”上,将“房门”开着;一头拿在他手里,只要白鹳进了“房间”,就拉绳关门。
20日晚,老黄老徐,整夜未眠。
5月21日 归来
天刚亮,老徐发现,那只白鹳仍然站在楼顶。数个小时一动也没动,头朝着中心的方向。
老黄守在老徐的房间里,手里拽着绳子,眼睛盯着那扇门。手心上的汗,出了干,干了出。
近10时许,只见白鹳突然展翅,一俯身,稳稳落在中心的碎石路上。
老黄乐坏了,正想走出房间,白鹳突然腾飞,落在了另一栋5层楼的楼顶上。且一站又是两个多小时。
中午时分,白鹳终于再一次从楼顶飞下。这一次,落在了院子屋顶上。观察片刻后,又轻轻展翅,落在防护网上。
老黄眼巴巴看着白鹳,却不敢走出房间半步。他怕白鹳认生,会再次飞离。
白鹳见四周没有动静,从防护网上飞到了地上——距离另两只白鹳很近了。
这时,老徐轻轻走进了院子。两个多月来,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给白鹳送食物。
果然,白鹳见他到来,不飞也不避。老徐只用手轻轻一赶,这只白鹳就进入了它们的“房间”。
老徐赶紧把门拴上,转身看,这只白鹳正在池里喝水呢。
中心员工把这个事件戏称为“越狱”。汪志如算了一下,个头大的白鹳,在外面呆了25个小时。
虽然把大家吓得不轻,但汪志如却窃喜:“说明这3只白鹳,野性未泯。放飞成功的把握很大。”
这也印证了他们的救治理念和方法是完全正确的——
救护中心的人,尽量少跟它们接触。“特别是刚出生的小鸟,如果人跟它们接触多了,它们对人的依赖性会大大增强。”汪志如只让老徐一人给小鸟送食。送食时尽量不把鱼虾倒入小盆内,而是放入水池中,让它们学会觅食、抢食。“救护野生动物的目的,是让它们尽快回归大自然。我们中心,不是它们永久的巢。”汪志如说。
6月17日 还巢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且行且珍惜!
”
送3只东方白鹳回家前夕,汪志如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句话。
的确,3只白鹳的去留,曾让汪志如很纠结。两种观点在他脑子里经常“打架”——
一种是,继续人工饲养。因为江南已经进入汛期,水位在上涨,现在放归,白鹳到哪里找吃的?再说,白鹳是冬候鸟,大部队已经北迁,没有大种群在这里, 3只小白鹳怎么活?
另一种是,尽早放归大自然。因为人工饲养时间越长,小鸟对人的依赖性就越强,失去了野性,就失去了野外生存的本领。
最终,汪志如选择了放飞。鄱阳湖水位上涨,可是还有农田、山塘;大种群北归,但近年来江西陆续发现有东方白鹳在鄱阳湖地区繁殖、度夏。
6月初,汪志如接到张丽君电话。张丽君说在梓埠镇农田的铁塔上,又监测到两个东方白鹳的大巢,一个巢里也有3只幼鸟,双亲及幼鸟均平安;另一个巢里有两个蛋,有一只大鸟日夜守护。
这个消息坚定了汪志如放飞3只被救白鹳的想法:宜早不宜迟!
他还不放心。6月9日这天,他特地赶往梓埠镇,在白竹、施家、丁家等村之间的铁塔上,一只大鸟守护着巢内一只幼鸟,另一只大鸟带着另两只小鸟飞到田埂上觅食。“要赶紧放了,不然眼前这些小鸟都要飞走了!
”他喃喃自语,“就到这里来放飞,说不定被救的3只小鸟,会很快融入这个家庭。”
为了3只被救小鸟的安全,汪志如给它们装上了轻巧的卫星跟踪器。经过多日观察,3只幼鸟体征正常,跟踪器工作正常。
“我们把小白鹳放到梓埠去,它们就有可能跟其他种群融合,就可以跟着成鸟学习各种本领。所以,要说担什么风险的话,我来担!
”汪志如很自信,“我们救护的目的就是让它们回归野外,而不能把它养成动物园里的动物。退一万步想,放归后即使有风险,我们也可以把它们一个个找回来!
”
这一刻终于来到。6月17日,3只小白鹳被人工救助70余天后,重新回归大自然。(江仲俞 杨碧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