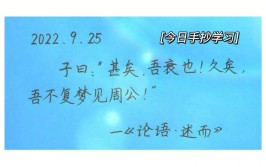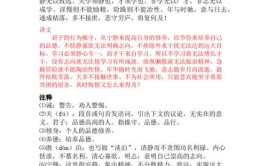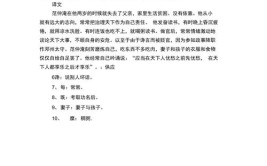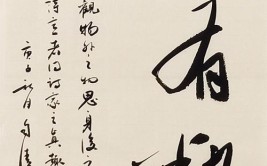旧有周公台面貌如何,历史没有留下图片,即便是《宁阳县志》,也只是用文字释名,所以至今不详,只有遗址存在。最近,周公台村人马保贵,根据自己童年记忆,画了一幅《南关旧貌示意图》,反映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周公台及其周围的地貌状况。从图上可以看到,昔日的周公台与今天的周公台大有不同。
周公台本是一座高大而宽广的土台,筑就高出地面多少米,至今未知。但经过三千多年的风雨剥蚀,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有高出地面(地面海拔60米)3米以上的“安山头”。当地居民传称此台为点将台,是周公东征时操练士兵、出征前祭祀天地的地方。蛇眼诸泉汇流而成的河,遇到大雨则从周公台四周流过。居民称,安山头是躲避水患之处。
安山头属于周公台的一部分,在台的东北部。其南北长约50米,东西宽约70米,东北角凹进呈月牙形,顶上平坦。1958年建水磨闸发电时作业人员在附近挖到很多兵器铜箭头(铜镞),1975年曾在此出土周代陶片。1971年,河河道改造取直,挖去了安山头,使河水穿过周公台东部原安山头处南流。河道疏通后取名宁阳沟,河一名消失,安山头亦不复存在。

铜镞
在安山头以西之周公台上,建村者整理台顶土地,建房筑院,长期居住下来,这就形成周公台村。该村建村时间不详,村内现有东西街1条,有苗、马、王、张、孙、李、杨等姓氏,居民不足百户。村西北角曾有宋代始建的周公庙,1949年以后拆除。
多年来,由于县里在此大搞水利建设,建闸立坝,挖河修渠,加之村民常年取土,高台基本夷为平地,今日的周公台已经失去旧有模样。
二、周公台是周代遗址1975年3月,县文化馆馆员马广前等人在周公台村周围发现战国瓦片等,认为周公台是商周时期的遗址。1980年5月,宁阳县图书馆、博物馆原馆长李登高对周公台遗址进行了调查。考察得知:遗址南北长400米,东西宽500米。发现遗址处较周围耕地略高,宁阳沟南北穿过遗址东部,周公台村建在遗址之上。村北、村南陶片极为丰富,村北堆积厚约0.5米—1.5米。暴露遗迹遗物有红烧土、陶片、石器等。采集标本有绳纹筒、板瓦片、夹沙灰褐陶鬲足、鬲口沿、泥质灰陶豆把、豆盘等。据出土文物断定,周公台属于周、汉时期的遗址。
周公台遗址,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时遭到破坏,特别是村北和村东南的遗址部分损毁严重。目前,周公台遗址尚存。
三、周公台在《宁阳县志》中的记载
宁阳创修县志始于明朝万历初年,至清朝乾隆八年,共已修成4部。在所修这4部县志中,没有收入周公台。从乾隆八年的《宁阳县志》开始,直至后来的县志、乡土志,计5部志书中,都载有周公台。
乾隆八年(1743年)《宁阳县志》,由知县李梦雷主修,其中卷之一《方域志·古迹》是这样记述周公台的:“东台,在县南里许。相传周公居东,系《易》于此,故又名周公台。案:周公居东,先儒皆谓‘避居东都’,惟《子贡诗传》、《申培诗说》言居鲁。证以宁土传袭,似居鲁为近是矣。”
咸丰二年(1852年)刻本、邑人黄恩彤总纂的《宁阳县志》也记载:“东台,在县南里许。旧志云,相传周公居东,系《易》于此,故又名周公台。案:周公居东,先儒皆谓‘避居东都’,惟《申培诗说》以为居鲁。以东台证之,似居鲁近是。”
从先后两部县志记载可以看出,“咸丰志”沿用了“乾隆志”的说法,只是“咸丰志”在证据中删去了《子贡诗传》,但都记载周公台的确实横世。县志对周公台的记载,与周公台遗址与时仍在,是一致的。
对《子贡诗传》一书,未有查到内容。《申培诗说》中,关于周公“居鲁”,仅有三处提及,说“周公居东”为居鲁:
(一)周公作《鸱鸮》是在“避居于鲁”时。《诗经》有篇《鸱鸮》,即“鸱鸮鸱鸮!
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飘摇,予维音哓哓”。《申培诗说》中对《鸱鸮》解说为“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周公避居于鲁,殷王禄父遂与十七国作乱。周公忧之,作此诗以贻成王,欲王省悟以备殷。全篇以鸟之育子成巢者,比先王之创业而代之为言也”。
(二)鲁人写《九罭》是舍不得周公离鲁归周。《诗经·九罭》曰:“九罭之鱼,鳟鲂;我觏之子,衮衣绣裳。鸿飞遵渚,公归无所,於女信处。鸿飞遵陆,公归不复,於女信宿。是以有衮衣兮!
无以我公归兮!
无使我心悲兮!
”《申培诗说》对此诗解说是“周公归于周,鲁人欲留之不可得,作是诗”。
(三)周公居鲁,鲁人作《狼跋》称赞他。《诗经·狼跋》是“狼跋其胡,载疐其尾;公孙硕肤,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载跋其胡,公孙硕肤,德音不瑕”。《申培诗说》对此诗解说为“周公居于鲁,鲁人睹其德容而作是诗”。
以上三首诗歌,都用申培之口,说周公在鲁,而且周公受到鲁人的赞美与挽留。
《申培诗说》,一般认为是明朝嘉靖年间进士丰坊伪作,但据台湾著名经学家、文献整理和目录学家林庆彰教授考证,则是王文禄抄袭丰坊之父丰熙《鲁诗正说》而成,与丰坊无关。然而,不管是伪作还是抄袭,《申培诗说》在明代形成,就有各种因由,那时作者应该占有不同文献资料来作依据的,只是想利用古代名人之口说出来使世人确信无疑罢了,不会是空穴来风。
但是,《宁阳县志》对“周公居东,系《易》于此”之事记载是“相传”,都是依据《申培诗说》揆度“似居鲁为近是”的,没有纸质可靠资料作依据。游唤民等著《元圣周公全传》中认为,“所谓周公‘居东’”是“外抚诸侯”。且论述“居东”的时间不长,“可能在(成王元年)六、七月至九、十月,大约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周公查知“三叔”(管叔、蔡叔、霍叔,主要是管叔、蔡叔)与武庚正在加速勾结,叛乱已不可避免。于是,周公日夜兼程努力做诸侯工作,又到殷时的王畿地区怀柔、分化殷人贵族。因此,县志记述的“周公居东,先儒皆谓‘避居东都’”中,先儒所言周公居住东都成周是对的。“周公居东”期间,周公遑遑忙于“救乱”,难能来在周公台“系《易》”。可是,东夷这里有周公台,周公“救乱”时不来,其他时间会来。
四、周公台与宁阳县城今宁阳县城始建于南北朝之北齐。周公台北靠宁阳县城,距旧县衙1公里。
北齐天保七年(556年),在今宁阳县城位置侨置平原县,今宁阳县城就是当年的平原县城。从北齐开始,后历隋代开皇十六年(596年)改名的龚丘县、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省称的龚县、金朝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复汉旧名的宁阳县,县城都在今址,至今县城未有移动,已有近1500的历史。
西汉的宁阳侯国都城,东汉的宁阳县城,都设在今泗店镇古城村址上。那时,今古城村址是鲁国的原宁乡之地;而北齐侨置的平原县选址,则改设在其北“十五里”(咸丰二年刻本《宁阳县志》)的今县城址,这应与周公台巍巍于世有关,也与(成)郕侯国有关,也与龚丘小国有关。
遥度当年县城定址起因,虽未发现文献资料记载,但经研究分析认为,建立新县城,选择新县城位置,关注到了此地历史遗迹,有依然屹立的周公台,还有西周成国旧都。
当时的周公台,肯定是高大且宽广的,绝对是庄严而神圣的。周公台是历史的珍存,所以朝廷与地方视此为天机之地,期盼县城立而崛起,就选择了周公台后邻,在这里筑起了平原县城。古城(西汉宁阳侯国都城)、周公台、县衙、成城,南北遥相呼应,一脉相通。周公台居中,挑起佑城重担,突显了其存在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县城居地,东、北方向河渠之水汇流于此,且又多泉,是风水宝地;东北临近成(郕)侯国,遗迹犹在,灵气尚存;周公台在县城南面,依偎城前,历史遗留,年代久远,是镇城之宝。周公台在前,县城居后,成(郕)为邻,三者关照,永永万年。宁阳人聪明多智慧,为国家多次提供行业经验,就证明了当年选择的城址是正确的。南临曲阜,北依泰山,环境优美,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安居乐业,宁阳是个好地方。
五、周公台与成、郕、盛成国,西周诸侯国,伯爵,在宁阳县城东北,地点临近宁阳县城,距周公台约3公里。郕、盛,是后来“成”改称的国名。周公台与成、郕、盛,有着密切关系。
(一)西周的成(郕)
《史记·管蔡世家》记载:“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载。”同篇又载:“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武于成……。” 由此可知:叔武是文王之子(《史记卷三十五考证》有载:文王之子长次顺序“各书不同”,贾逵等对长次皆言“马迁之言多辟缪”);武王克殷后封叔武于成。
《辞海》词条说“郕,古国名。姬姓,始封之君为周文王子叔武。故址在今山东宁阳北,《春秋》隐公五年(公元前718年)‘卫师入郕’,即此”。《辞海》似把叔武的“成”与春秋时期的“郕”相混淆,因为举例出自《春秋》。
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在《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上、宁阳县城东北临近处,标注有“成(郕)”,为诸侯小国。这就是叔武的成国。
《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成(郕)”在宁阳
以上记载说明,周公台东北不远有成国,是西周初期所封叔武的诸侯小国。
以史籍考证,“封叔武于成”之“成”在哪里?《史记·管蔡世家》中杜预对此说“东平刚父县有郕乡”。
杜预是西晋人,西晋时宁阳省并,刚父县(此时县名是否是刚父待考)属东平国,所以杜预称“东平刚父县”。东晋时刚父县已改称刚平县,南北朝北魏复立刚县,历代的县治都设在今堽城镇堽城里村址上。那时,刚父县西南有“郕乡”,就在今宁阳县城附近,这里应该是叔武之成国。后来,“成”改成了“郕”,因而西晋时已有“郕乡”。史籍记载的西周初年宁阳县城附近成国的地理位置,与《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是相同的。
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郭克煜先生《郕国历史初探》中提到:1975年陕西岐山县发现早周时期的一片甲骨,上刻“宬叔用”三字,断定“‘宬’‘郕’通用”、“宬叔当是宬之叔武”;又有,1975年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发现一座铜器窖藏,其中有“成伯孙父鬲”1件,说“此鬲乃是成伯孙父为亡妻所作的祭器”,断定“成,经传作郕,周武王弟叔武的封国”;据此就最后断定,“成国最初应在畿内”。
文王那么些儿子,要封不能只封叔武,由“宬”和“成伯孙父鬲”就断定“成国最初应在畿内”,认为是有些不妥。
宬,汉许慎《说文解字》解说为“屋所容受也”,清段玉裁《注》“宬之言盛也”。《辞海》对“宬”增加义项是“藏书室。专藏帝王手笔、实录、秘典等的地方。明代有‘皇史宬’”。查过多部字词书,没有发现“‘宬’‘郕’通用”的情况。显然,“宬”不是“郕”。“成伯孙父”是谁,是叔武还是叔武子孙?查郕国《君主列表及在位年份》,不见其人。笔者认为,不可以见到“成”字作人名或者作地名,就认为与叔武有关。因此,叔武的成国不可能在岐山县,还是应该在今宁阳县境。周公旦和成叔武,都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两人同在今宁阳县城附近,为西周之保障。
说文解字
叔武被封于成,《史记·管蔡世家》说,在“武王克殷后”。分析认为,应在周公东征胜利后。因为克殷之前东夷是殷商的地盘,不是有周一朝的天下,不会也不可能把叔武封到东夷来。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郕(盛)、成(郕)
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图《春秋·齐鲁》上,除了宁阳县城东北临近处标注“郕”(诸侯小国)之外,今宁阳县东庄镇境内“故城”位置标注“郕(盛)”,为城邑;图《战国·齐鲁宋》上,只在“故城”位置标注“成(郕)”,为诸侯所封的封君。
从地图上可以见到,当然还有文献资料证明,大约春秋时期,周公台东北的郕在今东庄镇境内“故城”遗址上另设了城邑,也叫“郕”。后来,此“郕”曾改名“盛”。战国时期,周公台东北的“郕”已废,“故城”的“盛”改名“成”,此“成”又改为“郕”。“成”、“郕”都是诸侯所封的封君。
《春秋》一书,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所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记述时间是,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此年为东周平王43年),下讫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此年为东周敬王39年),共242年。记述内容主要是,周王朝、鲁国和其他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朝会立盟、往来聘问,以及天地灾异等事。东周平王东迁在公元前770年,鲁隐公在位始于公元前722年。史书以《春秋》记述时间作为“春秋时期”,现在一般以平王东迁的时间作为“春秋时期”的开始。现在能读到的古籍中,关于成、郕、盛地名举例,都是以《春秋》记载为是。同样,为《春秋》作传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也都成为考证周朝历史的依据。
春秋时期,在“故城”设置郕邑又改盛邑。《春秋》隐公五年:“秋,卫师入郕。”鲁隐公五年见到了“郕”,这是对春秋时期“郕”的最早记载。鲁隐公在位是春秋初期,五年是公元前718年,这证明鲁隐公五年即春秋初期、在“故城”有郕国的存在,后来某一历史阶段改名为“盛”。春秋时期,郕是周公台东北的郕国在此新建的城邑。
战国时期,封君之城仍在改名。《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宣公四十八年,取鲁之郕。《正义》‘音城。’《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兖州泗水县西北五十里。’《说文》云‘郕,鲁孟(氏)邑’是也。”这里“兖州泗水县西北五十里”处,就是今东庄镇的“故城”遗址。齐宣公在位是战国初期,四十八年是公元前408年,这说明齐宣公时封君之城由“成”改名为“郕”,《史记》中记事则用了“郕”字。
郕城遗址
郕(盛)、成(郕),都夹在齐、鲁两个大国之间,逐渐沦为附庸。春秋初期,在鲁国控制之下;公元前686年降齐;公元前616年,国君去世,成为鲁国附庸;春秋后期,国君沦为鲁大夫;战国初期成为孟孙氏采邑;公元前408年,齐国灭郕,郕君失国。
有人说,成、郕、盛、宬相通,这是不对的。它们互相之间根本不是通假字,不是异体字,也不是谁是谁的本字,应该是不同时期的各不相同的地名而已。年代久远,资料匮乏,不去深入考证,所以就逐渐分不清,且以“通”而蔽之了。对于这个问题,研究《春秋》和“三传”是能弄明白的,应该下大力气才是。
(三)秦代的“成”聚落与两汉的“成县”
秦代对“成”记载很少,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秦·山东南部诸郡》,在“故城”址标有“成”,为聚邑。这说明,秦代“成”仍存在,是聚落。
《汉书·地理志》载:“泰山郡……,县二十四,……式。”《后汉书·刘盆子传》有:“刘盆子者,太山式人(唐章怀太子贤注:式,县名,中兴县废)。”刘盆子,式县人。其祖父宪,元帝时封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国除。刘盆子,西汉末年赤眉军领袖,公元25年被樊崇拥立为皇帝,年号建世。对式县,疑在“故城”。据考证,式,似为“成”之误,或是成县前称“式”。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定为“无考县名”。
《后汉书·郡国志》载:“济北国,五城,……成,本国。”济北国有成县,成本是旧国名。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为“成县”,属济北国。志与图的标注是相同的。
两汉时期,均设有成县,“故城”遗址今存城墙上发现汉代瓦片等就是证明。东汉以后,成县消失。
成、郕、盛,不管是国、邑、县,还是聚落,从西周到东汉末,在今宁阳境内存世1200多年。不难想到,宁阳这个地方是多么的重要与神圣。
周公台的筑成,会早于成国的设立,因为封叔武于成在周公东征以后。成国的选址,与周公台的存在是联系在一起的。周公以周公台为征伐东夷的战略要地,并由此取得了东征的全面胜利;周公台东南不远有鲁国,鲁国可护佑这片地区;周公台东北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河多泉涌,水源充足,是个优选之地。这些,都是成王封叔武于成而选择这里的理由。
六、周公台与龚丘龚丘小国在今县城东南10公里,亦即周公台东南10公里。
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兖州府志·古迹志》记载“故龚丘城,《路史》‘龚丘东南二十里有故龚丘城’”。清朝康熙十一年(1672年)《宁阳县志·古迹》也记载“龚丘城,《路史》‘龚丘东南二十里有故龚丘城’”。这里所说的东南二十里的“故龚丘城”,就是龚丘小国的都城。平原县改称龚丘县,即因龚丘国名而来。其遗址,在今宁阳县城(周公台)东南、乡饮乡沈家屯村东。遗址南北长750米,东西宽700米,今存城址夯土台高6米。
龚丘小国与商末箕子及其后裔有关。
箕子,名胥馀,是帝乙的次子,纣王的兄长,其明达事理而宅心仁厚,性格固执倔强。曾任太师,被封于箕(今山西省太谷东北),子爵,因名“箕子”。殷商王朝在纣王的统治下,走向穷途末路。面对此况,在王叔比干被纣王挖心、长兄微子逃亡的情况下,箕子痛苦不堪,便装疯卖傻,混迹在奴隶中间。纣王怀疑有诈,将箕子囚禁起来。经牧野之战,纣王登鹿台而死,殷商灭亡,箕子被武王从牢狱释救。武王深知箕子的忠诚和贤明,希望箕子辅佐自己,为新生的周政权出谋划策、治国安邦。但是,箕子崇尚气节,婉言谢绝了周武王的重用之意。后来,武王向箕子求教,箕子将《洪范》治国安邦的“九畴”大法献给了武王。《史记·宋微子世家》说:“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武王没有再挽留箕子,将其封到朝鲜半岛。箕子遵命,在朝鲜半岛创建了朝鲜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朝鲜《三国史记》把箕子作为古朝鲜建立的第一个国王,朝鲜古籍《海东绎史》亦有关于箕子入朝治国的记载。
箕子像
根据《龚氏族谱》记载,箕子十四代孙际元,被进贡于周。周桓王姬林(春秋时期之东周继平王后的第二个国王,前719——前697年在位)封际元于供丘。又载,际元之子坚作晋国大夫。从时间上分析便知,际元被封、坚作晋国大夫,是在东周的春秋初期。也就是箕子在朝鲜半岛300多年后,其后裔际元回归的祖国。春秋时期,供丘是小国,际元被封后不长时间改供丘为龚丘。周王赐际元之子坚以国为姓,改原来子氏而姓龚。因此,龚坚是龚姓的始祖,从此天下便有了龚姓。
际元是武王所灭殷商子姓后裔,为什么把他封在供丘小国呢?原因大抵有二:
一是供丘东南不远有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被封之地。箕子臣服西周,并为武王献“九畴”大法,有恩于周,其后裔靠近周朝要地,会得到周王的恩惠,会得到鲁国的扶持。
二是供丘西北有周公台,对供丘是一种保护。供丘位于鲁国、周公台二者之间,与两地之间的距离基本相等,这就便于国家交流,更利于国家安全发展。
周公台建在西周初期,龚丘小国存于东周初期,都在有周一朝,都发生在今宁阳县境之内,所以宁阳地区在周代是战略要地,也是不可遗忘的圣地。
七、周公台是周公的台周公能到周公台,只能在其摄政期间和还政之后,主要的还应该是东征践奄时期。
(一)周公摄政期间
殷商末,经牧野决战,纣王大败,在朝歌鹿台自焚,商朝灭亡,周武王建立了夏朝。夏朝初始,武王疾逝,成王幼立,周公摄政。此时,殷顽武庚蛰伏欲动,管叔、蔡叔心有不满,王廷危急。面对这一严重而复杂的局势,“周公临大难而不惧,处大变而不惊,断大事而不疑,进退从容”(《元圣周公全传》),因而出现周公亲拥成王率军东征之役,对叛臣进行讨伐。
伏生《尚书·大传》中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这基本概括了周公辅佐成王代理朝政期间的历史功绩。其中,“克殷”、“践奄”是周公东征。
“一年救乱”的“一年”,是指成王元年(前1042年);“救乱”是说周公首先做好召公和姜太公的工作,并得到他们的支持,然后外抚诸侯,也就是《逸周书·作雒》所说“周公、召公内弭兄弟,外抚诸侯”。这年中,周公活动于京畿地区和各诸侯间,稳定了国家局势,故称“救乱”。
“二年克殷”,指成王二年,周公奉成王命、在救乱的基础上一鼓作气彻底平定了“三监”和武庚的叛乱。武王克殷建立了西周王朝,周公平定武庚妄图复辟殷王朝的东方大叛乱是第二次克殷,故有“二年克殷”之说。据《元圣周公全传》作者游唤民分析,大抵在成王元年底或二年初正式东征。东征中,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做法。“三监”是罪魁祸首,首先讨伐“三监”。管叔被封于管,即今河南郑州;蔡叔被封于蔡,即今河南上蔡县;霍叔被封于霍,即今山西霍县。周公统帅东征军,先沿渭水、黄河以南向东进发,在今洛阳一带与“三监”对峙。进攻之时,霍叔消极对待,管、蔡难敌东征军溃退黄河以北。周公再北伐朝歌的武庚,把会合的管蔡和武庚叛军打得落花流水。武庚北奔被东征军截获处死,管叔自缢而死,叛军覆灭。即如《逸周书·作雒》所说“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
“三年践奄”,即成王三年、周公平定“三监”和武庚叛乱后继续东征,讨伐东夷。奄在东夷中势力最强,周公重点攻奄,即所谓“三年践奄”。这里所说的“奄”,实际上包括东夷的所有部族和方国。奄国在今山东曲阜,东征军把它作为主要打击对象。
“践奄”的过程,大抵这样:首先成王及周公率领包括“殷八师”在内的东征军由淮水顺流而下,讨伐以徐为首的淮夷诸国,即《尚书·蔡仲之命》所述“成王东伐淮夷”,并很快被东征军征服。接着,又征服了处在今山东、江苏间的祝融族楚国。然后,挥师北上,与太公所率军队共同攻灭丰伯与薄姑(蒲姑)。丰伯(丰白)国在今曲阜西南,离奄不远;薄姑在今山东博兴、临淄一带,都城在今济南东北,离海不远,南和奄隔着泰山,其在东夷中也是势力较强的大国。最后,把奄作为主要打击对象,集中军力攻下了奄国。“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薄)姑”(《尚书·蔡仲之命》)。这时,成王在奄,知伯禽在战斗中英勇顽强,立下大功,便把奄地封给伯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玮璋教授说,“鲁的地望原在今河南鲁山,东征之后迁至今天的山东曲阜,已发现鲁城遗址”,这与历史记载是吻合的。
灭奄中,追杀牧野大战中纣军的指挥官飞廉,直到海边把他杀死。在讨伐强国的同时,也灭掉了其他众多东夷小国。至于“践奄”所用时间,众说纷纭,不一而足,一般认为是历时三年。
周公东征壁画
征服了奄国,东征结束。
从以上分析可知:“一年救乱”之时,周公抑或不能来周公台“系《易》”;“二年克殷”之时,主要战场在河南,消灭对象是管、蔡和武庚,克殷是目的,东征军没有打到“东夷”地方;只是“三年践奄”之时,周公长时间在东夷,周公台在其征战活动范围之内。因此,周公在周公台操练军队、在此屯兵的民间传说不是信口雌黄,而是确有历史事件证实。并且讨伐前的占卜、祭祀,必定在周公台举行。
周公台在奄西北,距奄不远,其周围地势平坦,河泉汇集,粮草不缺,周公在此筑台操练军队伐奄,是完全有可能的。否则,怎么会有久传不衰的周公台呢。
《尚书·微子之命》中记载:“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这里说,周公是在东征中得到了嘉禾,不是在其他时候、其他地方得到的嘉禾,所以在指挥军队作战中更加竭力执行成王命令。
《史记·周纪》也载:“晋唐叔得嘉穀(郑玄曰:‘二苗同为一穗’),献之成王,成王以归(一作‘馈’)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东土,鲁(作‘旅’)天子之命。”此处“东土”的“兵所”,或指周公台。若如是,嘉禾则被送到了周公台。于是,嘉禾与周公台结了缘,嘉禾与宁阳结了缘,嘉禾与嘉禾园结了缘。华宁置业建成嘉禾园,传扬周公精神,承继嘉禾文化,嘉禾在宁阳复兴,这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
“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这四年中没有战争,周公来周公台会有机会。特别是制礼作乐时期,传说的周公在周公台“系《易》”,是能做到的。住在此地,有各种良好条件,地理位置优越,生活环境优雅,人际关系融洽,是离开成周而选择的好去处。不难想到,周公台东南有鲁国在,周公为国谋划、制定各种制度,会选择周公台作为落脚之地。
(二)周公还政之后
成王七年十二月,东都洛邑建成,举行庆贺和成王正式执政仪式,周公摄政七年后还政于成王。
周公既归政,居洛邑,主管东都,治理天下四方诸侯。三年后,周公退隐于丰(在今陕西西安西南、户县东)而逝世。成王十年(前1033年)周公辞世,享年61岁。
周公还政以后,作《立政》告诫成王官人(即选用人才)之道,作《无逸》告诫成王为王之道。除此而外,周公从还政到病故近三年时间里来周公台也是正常的,毕竟周公台是周公曾经居有的地方。
关于《宁阳县志》记载“系《易》于此”一语,此事至今难以断定。今传《周易》,儒家亦称《易经》,是周文王根据伏羲“先天八卦”演绎出“后天八卦”,又进一步推演出六十四卦,并做了卦辞和爻辞。目前,还没有发现周公为《周易》作注解的历史文献资料。没有文献资料佐证,只能存于不灭的传说中。
宁阳周公台村
但周公台作为地名,在全国他地未有发现,只在宁阳域境永存,世上绝无仅有。《宁阳县志》载有周公台,并据传说证实周公曾驻扎于此,县志中也确实记载。诚然,毕竟周公与周公台出现在三千多年前,加之古文献资料对此乏记,所以研究起来非常困惑,难以得到证据确凿的答案。
看来,周公台在周公东征中与他地相比不是举足轻重的要地,在此也没有发生过震撼征程、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也就很难将周公台名字载入西周史册,只是留在当地人的记忆、传说中。但是,周公台至今存有遗址,县志亦有记载,这些都是无可置疑、永远改变不了的事实。
参考书目:
①乾隆八年刻本《宁阳县志》 李梦雷主修
②咸丰元年重修《宁阳县志》 黄恩彤总纂
③《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 1975
④《二十五史》之《史记》司马迁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书店 1986.12
⑤《二十五史》之《汉书》班固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书店 1986.12
⑥ 《二十五史》之《后汉书》范晔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书店 1986.12
⑦《四书五经》[战国]孟子等著 中华书局 2009.1
⑧《图说天下》 龚书铎 刘德麟主编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5
⑨《元圣周公全传》游唤民等著 新华出版社2014.11
转载自周公嘉禾家风展览馆,如有侵权,请后台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