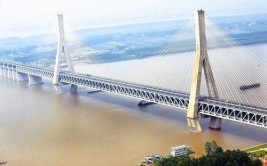这种以桥在溪前为桥名,是比较少见的。初到万州的人,总是以为大桥溪是指溪,而不把它作桥名理解。
大桥溪通车后,人们认识到了它的发展潜力,就在马路边修房定居,开店做生意了。
大桥溪,又是指一马路上的一段地方,是地名。从大桥溪桥的东面至三峡柴油机厂止的这一段公路叫大桥溪正街,公路的北面有一条巷,叫大桥溪沟。大桥溪正街和大桥溪沟行政区划上叫做东城办事处一所三段,后来又叫做大桥溪居委会。

文革时期,公路被统一改为红卫路时,大桥溪正街消失了,成为一马路中的一段。
1983年万县市将红卫路统一改为一马路。大桥溪正街这一段也就是一所三段一组
五十年代末钟鼓楼的一场大火灾后,段上便采取了相应的防预措施,每天旁晚轮流由各家派出一人,提着防火值日的牌子,挨家挨户提醒大家小心火烛,防火防盗。公路上,为减少交通事故,在路口也安排人在汽车来时,用喇叭提醒行人注意安全。
在六十年代,农贸市场就在公路两边,进城***农产品的人多,段上就在笔者家中设了简易的服务站,给人们提供开水,备有典酒、红药水之类常备药品,有人需要时免费使用。
那时,大桥溪正街最热闹的地方,要数晚上的茶馆,在有说书和竹琴表演的晚上,茶馆就会座无虚席,连路边也站满了听书的人,笔者那时还是小学生,为了听书,常常是晚饭后,就搬个小凳去茶馆门边守着,因为听书的人多,去晚了就没地方了。
后来,茶馆取消,门面改成了肉店。肉是供应的,每人每月一斤定量,凭票购买,居民有时为多吃点肉,就愿意买猪头,因为一个重六、七斤的猪头通常只需要两张肉票。于时,为了买到猪头,天不亮就得去排队,久了,人们就用砖头或烂物品在晚上放在肉店门口代替人排队,在肉店上早班的员工来之前,再才去排队,领取由肉店员工发的能购买猪头的号票,然后等到营业时间凭号和肉票才能购买猪头。笔者家就紧挨着肉店,与肉店员工较熟,有时还能开个后门,买点不凭票的猪骨头熬点汤喝。
笔者记忆中,大桥溪还有一个存放蛋品的仓库,每隔一段时间,仓库就会处理一些有问题的鸡蛋,有能吃的,便去壳后以每斤二角的价格卖给居民。在当时什么都凭票供应的年代,能买到这样的东西很不错了,也算改善一下生活。
大桥溪还有一个粮店,居民购粮都是凭粮票的,大米每斤一角四分二。那时居民供应的粮食是按六四比例的,即60%为大米,40%为粗粮。粗粮有苞谷、高梁、面粉、红苕等,供红苕对笔者记忆最深,因为在粮店购票后,还得凭粮店的凭证到距离几公里外的沙嘴河坝去取后挑回家才行。
豆腐店却是每天都要排队的地方,也是关门最早的店,开始居民持发的豆腐票购买,后来取消豆腐票,改为凭粮票购买,由于每天豆腐的供应量有限,就是排队也不一定能买到,所以排队就象在肉店买猪头一样的场景。
还有一个出名的饭店,叫做属荣饭店。最初的员工全是抗美援朝志愿军指战员的家属,饭店菜品价廉物美,很接地气,特别是饭店赵师傅炸的鸡酥子,味道独特,深受市民喜爱。
桥头北边自来水公司设有一水站,说是水站,其实就是一个水龙头,由段上安排一个老人守着负责收水票。各家取水都用自制的水桶去担水,五分钱一张的水票一担水,不分水桶大小。如遇停水时,在断水前,往往是水桶排成一长串,实在接不上水,那就只好到长江去挑水用了。后来,自来水公司推行几家可以联合装表将自来水接进户,挑水的人就少多了,水站在九十年代就完全停止了供水。
桥上的南边,有三位理发师,每天早出晚归摆摊为人理发,他们的手艺都不错,笔者小时候理发,就是由三位理发师轮流理的,理一次发的价格也只收一角钱。
夏天到来,溪沟是一群孩子玩水的地方,被称为梭滩,一群光屁股孩子顺着流水从光滑的石板上滑下,非常好玩。后来,牛奶场和食品公司的屠宰场建立,溪水被污染后,才没有孩子去小溪滑水玩了,而转到长江边去玩水了。那时夏天游泳,冬天在沙滩玩沙打沙仗一玩就是半天。
当夜晚来临,由于没空调,在公路两边都睡着一排排的人,八十年代开始,在路边睡觉的人就没有了,
改革开放后,大桥溪的居民也有了商品经济的意识,家家户户都打开大门,做起了生意。糖果店、副食品店、火锅店、水果摊等,一家连一家,为了在移民搬迁前多做生意,不少摊店通宵都不关门,使大桥溪成了一马路上最热闹的地方。改革开放,让大桥溪居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2002年,三峡工程蓄水前,大桥溪属于二期移民地方。全部居民被移民搬迁安置,老邻居也就分散了,多数居民因搬迁失去了联系。三峡工程蓄水后,大桥溪被水淹没消失了。但现在还有部分大桥溪的老邻居仍保持着联系,还时不时的相约,聚在一起喝点小酒,聊一聊过去大桥溪的人和事,感叹今天的美好生活,幸福满满的。
以下是大桥溪在淹没前的部分照片
大桥溪老照片(一)
一马路大桥溪段老照片(二)
一马路大桥溪段老照片(三)
(四)
(五)
(六)
(七)
大桥溪溪水流入长江(八)
(九)
大桥溪靠长江边的民居(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2021年11月11日大桥溪部分老邻居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