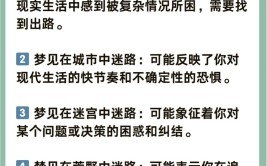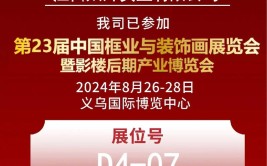雄起的来历
大约在一年前,见一报上有文章寻找“雄起”这一重庆特有的经典词语的由来,但一直就没见有结果。
我也不想贪天功为己有,心想,我们一条街那么多儿时的伙伴总有人会出来讲“雄起”的来历,只是时至今日未见有人出来说话,我也不想保持沉默了。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雄起”一词并不是现在才发明的,这句鼓舞斗志的“雄起”伴随着我们七星岗的一群小伙伴一起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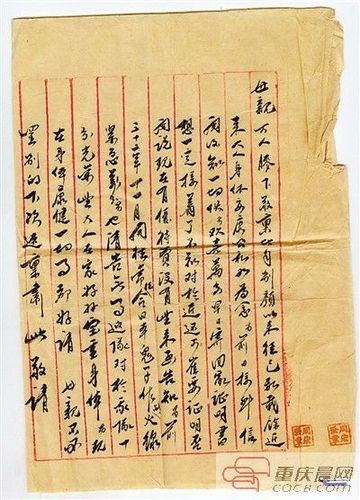
那是在我十二三岁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时期,没课上的我们整天在家无所事事。我家住在渝中区和平路自来水公司宿舍,我们那个宿舍大约有11户人家,因有很大的院坝,家家都爱养鸡喂鸭的。邓家有只七斤多的大红公鸡,我家也有只七斤多重的芦花雄公鸡,两只鸡都是非常的争强好斗,每次两只鸡在院坝里碰上就要撕打得难分难解。由于是“文革”期间,凡事都怕上纲上线,往往一句不经意的话都有可能惹出麻烦,何况是两只好斗的公鸡?这会从玩物丧志角度追查它的主人有无其它问题?所以两家的主人就很谨慎地对待自己宠鸡的好斗问题,绝不能因为它们的争强好斗而影响自己的人生前途。
而在当时,没有什么可供我们这些半大娃儿娱乐的事情做,有这么两只肯斗的公鸡,真是我们宿舍里的一件幸事。也不管大人的劝阻和恐吓,更不怕背上莫须有的罪名,反正只要大人不在,我们这群娃儿就怂恿两只鸡来斗,经常都是打得个天翻地覆的,让同样也是好斗的我们大快人心。
消息传出后,整条街的其他娃儿们也将自家的公鸡带来参加斗鸡比赛,因我们宿舍的场地好,适合斗鸡。看着越来越壮观的斗鸡场景,情绪激动的我们在每次的声嘶力竭中自然而然就喊出很多的啦啦词来,从最初的“打呀!咬呀!跳呀!”到不知谁发明的“雄噻!打噻!雄起噻!”。这不,到最后,竟然是很整齐的齐声呐喊“雄起!雄起!雄起!”那场面极为壮观,呐喊的声音也铿锵有力,好像不是在观看斗鸡,倒像是在观看一场扣人心弦的古罗马斗牛赛。
“雄起”,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应用广泛了,不光是为斗鸡,为打架的人助威,鼓励弱者坚强起来等场合逐渐都用上了“雄起”。只是,谁最先在重庆足球场上将“雄起”这句啦啦词喊了出来,尚无考证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是同我们儿时的玩伴有渊源的某个人,偶然把我们儿时在斗鸡场上流行的啦啦词用在了热血沸腾的足球运动场上,一下子得到了重庆球迷的认可,并继而由成都、由四川传遍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足球运动中。这恐怕应该说是我们对现代足球文化的贡献吧。
进厂当工人以后
那是一九七零年,国家开始大招工。那时招工都要搞政审,我们政审都搞过了,先听说被招到庆江机械厂,后来通知到了,又突然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七六部队第三四零三工厂,定于九月九日到小什字岳王庙发布。后来才知道当时这个破厂打起成都军区的招牌,强行从其它厂的招工人员手中把人家搞好政审的人抢走了,那时部队是老大,惹不起。
大约坐了一小时车到了厂里,先到大礼堂,还带起行李的就上第一堂保密课,然后就带到一间大约四十平米的房间去,一间房住十六个人。睡的是猪儿窖窖铺,大约半个月后床才发下来。全厂只有稍微像样一点的红砖厂房两栋,也就是电站下面、靠钢管厂那两栋。其余的都是后来陆陆续续修建起来的,特别是建二、七车间时把我们弄去挖土石方,我们很出了点力。
三四零三厂是一个破旧不堪的汽车修理厂,设备落后,厂房破旧,工人文化低;但那些工人的手工技术相当不错,因为那是一个老厂,解放前是国民党的汽车医院,所以很多老工人的手上技术简直不摆了。特别出名的技术有扳金、木模、电焊、汽修、电镀等。那时刚一进厂,那些老工人个个都来重复那些“地拉那的胜利,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对我们进行历史教育,厂史教育。接触工厂多过两天,熟了,就开始听老师傅讲厂里的这个那个的奇事、艳史、厂史。
其一,卫生所不卫生的问题。具体的记不到了,只记得有个开龙门刨床叫“和尚”的老工人,有一次拉肚子,到卫生所去看病,叫卫生所开假条。卫生所的医生也不是正牌医生,不给他开,但他确实拉肚子拉得太厉害,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拉,拉了一裤子。“和尚”现了丑,气得遭不住,为挽回点面子,他怪卫生所医生不作为,便用报纸把大便一包,跑到卫生所使力往桌上一搭,溅得满屋都是大便,臭气熏天,把人都笑死了。
其二,也就是那个医生,对人态度一贯不好,有人在卫生所的门上贴上一幅对联,上联是:好人医病;下联是:病人医死;横批是:死人医硬
其三,那个医生给她娃儿洗澡,要用开水冷了来洗。她完全是有洁癖,太爱干净了,她娃儿基本生活在无菌环境里,一点没有抵抗力,一得病发烧就遭病毒性感染死了。
其四,某车间有一个未婚青年经常讲别人空话,哪个女的偷人,那个女的不贞,还经常说什么“破瓢把,烂筲箕,各人有个方便些”来取笑别人。后来他找了一个全厂都公认的烂货,结果大家经常就把“破瓢把,烂筲箕,各人有个方便些”这句话挂在嘴边。
其五,此人结婚时不晓得哪个在门上贴了一幅对联,上联是:一个牛卵子,一个狗鸡、巴;下联是:一对新夫妻,两个旧行头;横批是:各人有个方便些。
其六,有一次厂里修的车开出去出了一个事故,死了一个团长,上级派人来检查修车质量,总结了几句,就是:修的车除了喇叭不响,其余的地方都响。
和平电影院老照片
跑勤通
一九七零年,我们市中区有一百一十个人,被招工进了土桥的一个汽车修理厂。那时候工作不好找,能有个工作不容易,所以特别珍惜。
那时候交通远不如现在这样方便快捷。我们一拨进厂子的人上班线路是从市中区到肖家湾,转车到杨家坪,再由杨家坪乘公共汽车到九渡口,再从九渡口过轮渡,下船后爬上河岸再到李家沱,然后再转乘车到王家坝。由于路程远,加上转车转船,上班就得早出晚归。
为了保证不迟到,每天上班都要准备至少两个小时的时间,还要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转车,转船,路上一点时间都不能耽误。如果赶掉一班船就要多等半小时。有时看到要迟到了,就去搭车渡,在车渡上再搭车就可搭到土桥或王家坝而不迟到了。为了搭车要给人说好话,免不了还要遭白眼,或者遭车渡上的工作人员吵骂,因为车渡上有危险,通常不允许一般乘客上车渡。
最后的车渡
那时人年轻,既要上班,又想每天回家好耍,于是每天一起跑通勤的就有二十多人,长年累月,在路上摆龙门阵,讲笑话,倒也快快活活的。
冬天下班要看天气,九渡口河边五零七发电厂烟囱冒烟的方向,就是最好的预报。其中向某几个方向飘倒没关系,如果浓烟向李家沱飘,就是第二天早晨要起大雾,为防第二天过不了河,就不要回家了。此“天气预报”准确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
那时候工资只有三、四十元,市郊月票五元,船月票两元,还有李家沱到土桥的车票钱,反正单位上只报销三元钱。盼星星盼月亮、盼到南坪到李家沱的水泥公路修通了,结果不通月票。如果走南坪要近得多,天天买票经济上根本受不了,盼改革盼开放,结果李家沱大桥修通了还是不通月票。在这前后期间大家纷纷跳槽,逃离-----逃离到不须跑月票的地方,我后来成功跳槽到了联通公司,我终于结束了跑月票的日子,万岁!
“文革”中的“武斗”
“文革”中所谓对立的革命群众组织搞“武斗”那一年,我还小,记得开始“武斗”双方的人员头戴藤帽,大约用两尺长的文斗棒,手持木盾牌,后来发展到打板凳弹枪(就是在条形板凳的两条腿上绑上粗大的橡皮筋,做成强有力的弹弓,这样的弹弓,可以弹射拳头大小的鹅卵石,故名“板凳弹枪”)。
“武斗”之前是“文斗”,当时位于解放碑的和平电影院(即解放前的国泰电影院,现已拆除)是红卫兵组织“8.15”的“东方红广播站’,而对面老交电大楼(现新世纪百货大楼及针纺站)则是群众组织“反到底”的“完蛋广播站”。武斗初期,我们经常到解放碑去看热闹,小崽儿啥子都不怕,能走好近走好近。白天双方广播站吼到吼到的竟约定一方下来几个人对打。打得鼻青脸肿、血沽淋裆的又往回跑,板凳弹枪打得鹅卵石天上地下乱飞。有时失手了,鹅卵石飞向看热闹的群众,大家吓得象鸭儿扑水,一潮一潮地跑,那场面真的是刺激得很。
晚上只辩论(文斗),不搞武斗,主要是要向群众宣传,拉拢更多的人加入到自己这一派所谓革命队伍中来。记得那时天天晚上去听两派广播站的辩论,那个辩论简直是五花八门,啥子都来,一会讲道理,一会读北京来电,一会放诗词歌曲,一会儿揭发对方派别的罪状,一会儿又进行人身攻击┄┄好笑惨了,简直比听评书还安逸。
那时的大字报也好看,漫画也画得好,我们晓得的好多成语典故都是那时学到的。有的大字报贴得有两寸厚,把收废纸卖得整肥了。
从“反到底”派的完蛋广播站被烧了以后,武斗升级了,开始打枪了。枪子不长眼睛,我们就不敢去看武斗现场了。
“武斗”期间老百姓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买定量供应的米、煤、油、菜比较困难。这个时候,就有了解放军专门武装押运送粮、油、煤的专车。对这样的专车,对立的两派都是不会抢劫或者扣留的。
“文革”中武斗后期值得一提的是出现了强盗武装抢劫居民的事情。那些社会流氓,小偷等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在武斗中搞到了枪,晚上就去居民区抢劫,一时把居民搞怕了,社区居民也自发组织起来,一有风吹草动,就相互报信,凭借人多势众来吓跑强盗。具体方式就是发现案情的人家首先敲起锅儿、盆盆,听到声音,大家都敲起来,相互声援,硬是把强盗给吓跑。
那时用敲锅、敲盆的声音来吓唬强盗的情形确实壮观。常常只要盆盆一响,远远近近好几条街都敲起来了。记得有一次是夏天,半夜一点左右,两路口最先开始敲盆盆,结果声援的越敲越响,越敲越远,从上半城敲到下半城,从菜园坝火车站敲到朝天门码头,又从朝天门敲到曾家岩,从大溪沟传到人和街,又传到罗家湾,传回上半城。有时一晚上敲上两道,直到凌晨五点多钟才结束,真的是整整折腾了一晚上。
那时候渝中区定量供应的菜油要到生产菜油的“解放区”江北区去买(江北区是反到底的占领区,号称“解放区”),地点在观音桥的老菜市场坝儿.那儿原来有桥,有水,有乡场的坝儿,还有一个很大的堰塘,一个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主城几个区的居民都要到江北去买菜油,人之多可想而知。为此,买菜油排队往往要排整整一天,但那时的人决不敢插轮子(也叫插队,北方话叫“加塞儿”),因为“反到底”组织派人端起枪在维持秩序,发现插队的就一顿吃膀顿膀的打一顿。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开发,已经不存在了,原来优美的环境消失太可惜了。
90年代的菜园坝火车站
那个时候我们还常到红旗河沟、观音桥一带的水田里去捞鱼。有时捞到一种叫“火烧泡”的鱼,鱼身上有虎斑一样的花纹,好看极了。拿回去用豆瓣瓶子喂养,用蚯蚓喂它。它经常从瓶里跳出来,干得像死了一样,但捡进瓶去一会儿又活过来了,命长得很。它一直活了两年多。
80年代的观音桥
记得有一次去打菜油时走到华新街,那时华新街还没开发,路两边还是田坎和菜地,一辆汽车开过时突然发出“啪”的一声响,而差不多同时,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把抱起的南瓜一甩,立马趴到田坎上,行动之快捷,简直比训练有素的解放军战士卧倒动作还要快。大概过了一两分钟,老太婆才慢慢地抬起头来,观看是哪里在打枪。原来这个老太婆是从“武斗”地区经过枪林弹雨锻炼出来的,估计是把“黄”司机加油太多、汽车回火的声音当成了枪声。此情此景,即使现在想起来还把我们笑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