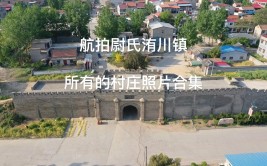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是1963年,记得那一年,春天刚刚来临,还不到清明,淅沥淅沥的小雨就下个没完,有的老农说,今年的小麦肯定会丰收, 就怕秋天又没收成了。到了麦收,果不其然,小麦的产量达到了农业发展纲要所说的“过了黄河”,也就就是说达到了五百斤。人们喜形于色。
麦收后,玉米谷子和高粱长势喜人,庄稼人盼什么,不就是盼有个好收成?然而,好景不长,到了农历的七月份,哗啦哗啦的大雨下个没完,连续降雨,这家的墙头倒了,那家的屋里漏水了,有的人家在屋里的炕上搭了窝棚。在我们村北五里地就是滹沱河,进入主汛期,年轻人都到滹沱河的大地上防汛去了,河里的洪水打着漩涡,汹涌澎湃,像脱缰的野马滚滚向前。当时我在离我们村五里之遥的豆店村上小学五年级,豆店村就在滹沱河大堤边上,中午放学后就到大堤上看洪水。一天,学校的周老师说:“课不能再上了,上游的防洪大堤决口了,赶紧回家,路上不许耽搁。”同学们踏着泥泞,一路小跑地回了家。当天晚上,无情的洪水就包围了我们的村庄,地里一片汪洋。听村干部们说,这是百年不遇的洪水,北大堤上是解放军在抗洪,为的是保卫津浦铁路和天津北京。没有办法,只有在咱们这里分洪了。全村的乡亲们在村干部和上级派来的工作组指导下,加固护村堤。
几天后,洪水不断上涨。都说是水向东流,然而,由于下游堵塞,洪水开始向西流,护村堤也保不住了。村干部把村里的五保户,孤老户转移到村里的最高处,整个村子几乎被洪水淹没了。水还在涨,地里的水已达到两米多深。当时村里的房大都是土坯房,晚上,唿隆唿隆的声音不绝于耳。当时年纪小,知道是倒房的声音,躺在窝棚里不敢动弹,天明了,看到村里的土坯房几乎无一幸免。

将近中午,天空飞来两架飞机,投下和信封一样的东西,飘飘扬扬,落在了村边。父亲说,可能是慰问信,我沿着大街水浅的地方跑了过去,原来扔下的是一袋一袋的大饼,每袋大饼里还有一封慰问信,村里水性好的把大饼从水里捞了出来,有八九十袋,给村里的五保户孤老户留了3袋,余下的就给人们分了。
都说是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我记得那年发大水是农历八月初三,多年的规律也不灵了。
洪水过后,人们忙着修补自己的房屋,倒房的,先支个简易房让老人和孩子们住进去。
记得那年,救灾物资源源不断的运来,大米白面,有大白菜,木薯和木薯片,芋头和各种从没见过的东西,天津北京派来的医疗队整天活动在村子里。受灾了,可人们没饿着,没渴着,没有疫情发生。
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说,要是在那旧社会,发这么大的水,不知有多少人流离失所,不知有多少人无家可归,又不知有多少人只好乞讨为生了。感谢***,感谢毛主席,感谢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来源河北农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