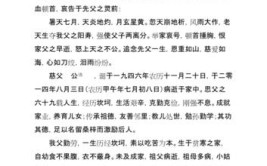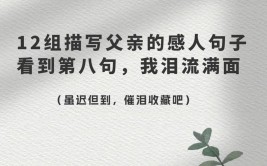砌屋记
文|林晓哲
1

1967年,父亲和祖父从虹桥买了一头牛。当时他们还不敢多想这头牛日后的大用。十岁出头的二叔成了放牛娃。三年后小牛长成大牛,生了一只小牛犊。这是大家熟悉的场景。多年前,曾祖就曾贩过牛。也是在虹桥,曾祖认识了另一个贩牛人。这个人日后成为他的丈人。曾祖与曾祖母养育了六个孩子,祖父居长。祖父与祖母又养育了六个孩子,父亲居长。人口愈来愈多,房子愈来愈小。父亲一家人住在一座老房子的宅门角里,三十多平方米,两个房间,两张床。很难想象,一家八口怎样挤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其中包括祖母、大姑和小姑。或许还可以说包括一只猪,那时刚刚引进的白猪,以及一群鹅。猪和鹅的起居也是在宅门角,来来往往,天天照面,几乎谈不上一墙之隔。我问,不嫌脏?父亲说,那时的人就是这么脏的。很脏的人也很瘦。但牛、猪和鹅,越长越膘。
父亲向来宣称自己十六岁当家。他在十三岁小学毕业后失学,失去成为家里第一个“乐中生”的机会。接着有两年“农中”的经历,记忆最深的已不是学习,而是将每日配给的米省下来,置入竹筒,由二叔带回家。二叔每日往返从村里到“农中”的路上,家里的米也积攒起来。村大队发现时,还被冤屈为偷米。紧接着的1960年,曾祖、曾祖母相继去世,一个未曾谋面的叔叔因盲肠炎而夭折。“搭食堂”在夺走我的三位长辈后结束。父亲把这一年视为他当家的第一年。那一年,他代替生病的祖父,跟随他的叔叔们去城北十八玍斫柴。寒冬腊月,父亲带去的米饭结出厚厚一层霜冰。
父亲的叙述伴随啃咬的动作,试图让我体会结着霜冰的米饭的滋味。不加糖的冰棍?父亲笑了。他说他从十六岁开始承受一个大家庭的压力。他想过上更好的日子。我很惊讶,激励父亲的居然是饥饿而不是家族曾经的荣耀,不是四对旗杆夹(考取功名的象征)和六百亩田产,不是耕读世家。而这些都是他常常拿来激励我的。父亲渐渐地结识了许多年长的朋友,他跟随他们尝试各种挣钱的方法。就像现在,父亲在生意场上有更多年轻的朋友一样。父亲至今还在挣钱,他拒绝像大多数的同龄朋友那样成为十足的老人。
年轻的父亲很快成为滩涂上钓跳鱼和踏蟹的高手,一斤跳鱼二角八钱,一斤蟹一角钱。也打零工,去玉环鹿西岛的滩头筛“苍蝇头”,一种绿豆大的石子,运回来铺路,一次赚十几块钱。从沙头、小门山进盐,再拿到温州永强兑糖,再把糖带回来卖,一斤糖三四角钱。母鹅孵小鹅,一只可以孵三四窝,一窝八九只,小鹅长到几个月,就乘船拎到温州街上卖,一斤鹅七八角钱。父亲把挣来的钱交给祖母。祖母把钱藏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有一天,祖父对父亲说,我们去买头牛吧。家里就有了一头牛。接着又有了一头猪。接着一头牛变成两头牛,一共卖出四百三十块钱。接着猪又长到五百斤,成了公社出名的胖猪,卖出三百多块钱。
牛和猪,多年来为祖母、父亲以及他的弟弟妹妹们津津乐道。二叔舍不得牛,挂过泪。但是它们的相继离开使父亲的大家庭一下子多出了七百多块钱。七百多块钱连同积攒的钱,成为父亲经历的第一次砌屋的启动资金。这一年是1970年,父亲二十六岁。这一次砌屋对父亲还有一份特殊的意义。父亲二十一岁和母亲订婚。他迟迟不能迎娶母亲。那座宅门角的狭小的老房子,没有办法在一个大家庭里再分隔出一个小家庭。我想父亲一定在心里盘算着砌屋的时间。屋子慢慢地从地上生长出来,待到它长成了,也就到了迎娶母亲的时间。
很快的,父亲和祖父与村里商量好地块。就在家族荣耀时祖屋的南面,是离当年旗杆夹最近的地方,至今滴水花檐、六角古井、青石槽、青石磨盘尚在。在那样一个单纯的农业时代,砌屋说简单也简单。木头搭梁,石头做墙,泥巴捶地,再盖上瓦,一座房子就差不多成了。木头,专程坐船去永嘉乌牛买,料好,便宜。石头,是老房子后的老鼠岩上采的,一家人齐上阵,一块一块搬过来,两三百米路。泥巴,是村后山祖墓附近的白石泥,也是一家人一担子一担子挑,四五百米路。但三间屋框架一搭好,隔墙也没做,家里的钱还是用光了。无奈,停工。一停大半年。到了秋收时节,村里的人便把稻秆堆到里边去。大伙说,空着也是空着。父亲于是又急着复工。连借带凑地复工。三间屋砌好,在西边添了一间简易偏舍。偏舍缺四根横梁,父亲便一个人跑到虹桥去买。
父亲比画着,一个人,四根三米长的横梁,怎么担回来。看我听不明白,特地拿来五根筷子,放在茶几上,彼此交叉着,在其内部构成一个三角形:底边一根代表扁担,两边各两根代表横梁,横梁交叉捆在一起,构成顶角,横梁再分别和扁担交叉捆在一起,两侧横梁在扁担左右的重量,需要大体平衡。父亲就站在三角形内保持大体平衡的支点上,从虹桥一路担到二十里外的翁垟。走到南岸,累了,坐下来原地休息。一个与父亲同龄甚至年长的陌生人向父亲问路。他对父亲的称呼是“阿伯”。
直到现在父亲仍对这一称呼耿耿于怀,直到现在父亲仍被更多人称为阿伯。父亲属鸡。母亲常常说,这只公鸡啊,爱打扮。父亲浓眉大眼,鼻梁高挺,不乏英气,但年轻的时候背就微驼,又黑又瘦,胡须很厚。母亲的评价是,看你那相道,不叫你阿伯才怪。
但房子终究是造好了。父亲从舅婆那里借了一张圆额床,摆在新屋里。这是为迎娶母亲准备的。几年之后,他们才拥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圆额床。这张床现在还完好无缺地保藏着。
有一天,父亲抡着锤子,跪在新房子里锤蛎灰坦。父亲的朋友顺木伯走进来,对他说:我们要办厂,晚上开会,你来吗?
2
从1971年开始,父亲就不再是单纯的农民。他最初和朋友一起办麻袋厂。做不长,改行办电器厂。这个厂,全称是乐清县电器三厂。作为集体发起人之一,父亲从来不知道一厂、二厂在哪里,连它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这个厂从十来个人,迅速地发展到五个车间,四十余人。但几年后又散了,许多人陆续从厂里出来单干。到1980年,电器三厂作为一家集体企业就不复存在了。但父亲留了下来。他所在的车间只剩下四个人。父亲带着剩下的三四个朋友,一直做到2002年。
起初,从电器厂领着固定的工资,家境慢慢地富裕起来,就不用再借钱,而是常常借钱给别人。父亲和母亲的做法是,五百,一千,几千,都借。借得长,就算利息,一分息。父亲和母亲深谙细水长流的道理。但父亲对电器厂相对清闲的生活并不适应。他用空余的时间跟一个朋友学会了做粉干,又把做粉干的技能传授给大家庭的成员们,祖父,祖母、母亲、大姑、二叔,等等。做粉干有复杂的工序,大家就轮流着上夜班。父亲通常是傍晚从电器三厂下班后开始磨米粉,揉成粉毂置入大镬烧,再转到碓臼反复揉搓,接下来用机器拉出粉筋,最后重新置入大镬烧熟,直至早晨八点前制成粉干。好几年的许多个夜晚,父亲都是这样度过的。之后匆匆洗漱,去厂里上班。母亲也操起副业。那时翁垟的矿灯和柳市的五金、白石的卵卵(石子)齐名,母亲就在家里装矿灯。装一百盏盈利二三百块钱。
父亲常说,家私要平时一点点做,钞票要用在关节头上。这么做着做着,进入1982年,就到了用钞票的关节头。父亲和母亲合计,砌新屋。
那时村里已经有两座三层楼。父亲原本也想砌三层楼。但砌三层楼,样式就只能简单。又和母亲合计,改砌一座样式好看的二层楼。第二年,父亲果然砌了一座全村最漂亮的二层楼。
父亲罗列着理由,带着证据确凿的自信:你看,五十厘米高的地丘,那时通常只有三十厘米或不做地丘;黑白的石英墙,以及磨出光滑表面的石英护栏,那时村里的房子都没有;窗户的四周,用一皮砖来锁边,也洒上石英,既美观又实用,窗台放上一只水桶也很稳当;西间靠近马路,装的四排门那时也没有开始流行,可以做店面;道坦的西南面的一层裙屋,屋内可以养鸡,屋上的平台和主楼相连,可以种养花草。母亲和大姐都是喜欢种种花草的,她们种了昙花、东南西北、鸡冠花、秋海棠、绣球花、君子兰,等等。这座房子,我们一家住了二十七年。砌屋时,我开始记事。到拆屋时,我请摄影朋友把房子的角角落落拍了个遍。大姐、二姐、哥哥也一起回家,来看最后一眼。砌屋前两三年,父亲和几个叔叔从祖父的大家里分离出一个个小家。到拆屋后,新宅落成,我也作为老幺,从父亲的大家里分离出一个小家。这样,这座二层楼房几乎完整地承载了父亲作为一家之主的岁月。他也是默默地承担着这样一个一家之主的职责。
崭新的二层楼让父亲心满意足。父亲已经不知不觉步入中年。他开始喜欢向我们念叨家族古老的往事,关于它的荣耀与败落。他也渐渐地感受到孤独,因为他的周边几乎没有朋友把精力放在子女读书上。20世纪80年代于知识分子而言是自由的时代,但对于大多数乐清人而言,那只是一个挣钱的时代。“一个挣钱的时代”出自小叔之口,以此作为他“乐中”毕业后就去经商的理由。对于小叔的经商,父亲是惋惜的。接着,敢闯敢当的三叔被“抬会”(本乡非法集资的一种形式)击垮,他迅速积累的财富顷刻间化为乌有。债主们占领了他的房子。父亲买下了三叔的房子。“林家的房子要守住。”向来不多管闲事的祖父这样告诫他。
之后,父亲做事愈发地小心谨慎。父亲说,那段时间,柳市首批有七家企业办了生产许可证。几个从电器三厂出来的朋友,也和父亲商议,重新聚首办许可证,但提到投资的数目,父亲退缩了。一个在黄华办开关厂的朋友来向父亲取经,也想和父亲合作,父亲依然婉拒。父亲其实也和朋友一起在上海办过厂,他投了几千块钱,带上了几个亲戚,但唯独自己没有去,还是守在电器三厂的老车间里。
上海的厂经营一年后停产。父亲的解释是形势紧张。电器三厂的业务也日趋惨淡。90年代初,应该有许多小生产作坊经历过同样的命运。我至今记得,当年在柳市街头,“上海开关厂”的标牌是称斤论两卖的。父亲不得不暂别干了二十年的电器生涯。他来到义乌。在第二次砌屋时,来自瑞安的泥水匠永盛叔常常找父亲攀谈,后来父亲帮他改行做了生意,再后来他又去义乌办了针织厂,永盛叔请父亲一起经营针织厂。但父亲在义乌的日子并不如意。他不会普通话,蹩脚的普通话只是乐清方言的离奇变异。原本不会抽烟,此后学会抽烟。也不会烧菜,却不得不常常自己烧菜做饭,尽管永盛叔的家人都在义乌。一年后,他还是告别了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回到熟悉的电器行业中。
父亲的电器生意仍是不温不火地做着,仍是骑着凤凰牌自行车,每日往返于翁垟与柳市之间。从门前,经过高阳、泥垟、汤岙、万里桥、东岙、长山、麻园,就到了柳市。父亲常常出入于电器城、正泰、德力西、金山门、泰成等厂家,购买变压器、互感器、断路器、刀开关、电流表等,再原路返回。那些年,父亲是一直骑着那辆自行车,但脚下的路在变,从窄小的水泥路到宽敞的公路,再到公路也渐渐窄小,摩托车渐渐多起来。接着摩托车少了,公交车和小车多起来,沿路的新房子也多起来,四层五层六层,甚至比六层更高的。父亲曾经的新房子也淹没在紧挨和簇拥的新房子中。它黑白的石英墙更显出陈旧的味道,以及橙红色窗户上脱落的油漆,长出墨绿色浮苔的阳台护栏。二层楼房子不可避免地老去了。在老去的过程中,大姐中专毕业到人民医院上班,二姐乐师毕业到翁垟一小教书,哥哥和我也到乐中直至大学,哥哥读会计,我读法律。父亲说,现在不和人比钱多,现在我家里有四个师,医师,教师,会计师,律师,这四个师,是最吃得开的。那几年,父亲也确实只是安稳地做着电器生意,收入也不多了,我和哥哥读书的费用,大姐和二姐都分担了一部分。1996年,重整旗鼓的三叔在乐清买房,劝父亲也买一套,那时我和哥哥都在乐中读书。父亲思考再三,回家把二层楼装修一新。再后来,三叔回老家盖别墅,他又说:“你看,老了还是要住回来。”
3
2001年,我和哥哥大学毕业,我在乐清,哥哥在温州。我和哥哥的工作没有让母亲操心。
我和哥哥的毕业,让父亲和母亲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家里的开支更加节省。母亲说“省吃俭用,何必求人”,父亲对菜肴向来是“多餐不剩”,而他们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就是把新烧的菜留给我们,自己吃剩菜。对此我和哥哥早就熟视无睹、心安理得。前些年,父亲一直抽十块钱的烟,我抽二十块钱的。有一阵子,我也试着换成十块钱的,但很快又换回来,面子上挂不住。于是劝父亲也抽好一点的,父亲拗不过,才换成十六块钱的。即便亲朋好友送来更好的烟,父亲也是换成十六块钱的,或者留着办喜事用。
父亲把为两个儿子置办房子视为自己应尽的责任,而且是必须完成的责任,不需要儿子参与的责任。他很快在电器三厂之外,和几个朋友在象阳办了一家包装厂,做产品的外包装和内包装。父亲又开始了两头跑的生活,从翁垟到象阳,再从象阳到翁垟。2002年,在朋友的劝说下,父亲第一次认真思考是否离开电器三厂。他已经在那里待了三十一年。父亲为它的兴建搬运过石头,从毗邻的运河里挑过河水。但父亲还是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电器行业上。同时,他也感觉到,需要克服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滋生的求稳念头,他的年龄使他在拉业务上常常处在劣势。有更多的年轻人上来了,比他小十岁甚至二十几岁的。父亲清楚现在需要更多年轻的朋友。相比于他们,父亲的优势在于从业三十多年的经验,在于做过电焊机、电焊机调节器、仪表车床、充电架、配电屏、高压柜、低压柜、变压器等十数种产品,一些产品还是乐清最先做的几家之一。他和电器行业的老朋友商量着、犹豫着。母亲也以行动表达对父亲的支持。就这样,父亲开始了第二次创业,转到柳市做成套电器。
父亲从没有提及他二次创业承受的压力。他平淡的叙述始终脱不了“朋友”这个词。他试图让我明白的,不是他为家庭或是孩子所付出和承担的,而是他跨出的每一步都是凭借朋友的帮助。他甚至否定能力,仅仅以“搭搭班”(跟班之意)形容自己。父亲确实接受过许多朋友的帮助。正如他也帮助过许多朋友一样。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往往也是他帮助过的朋友在帮助他。他对过往的苦难经历可以一笑置之,但说到朋友之间的互相帮衬时神情特别庄重。到柳市后,父亲仍在寻找新的机会。他年近六十时迸发出了远比90年代更加热烈的创业激情。父亲正是抓住了一个投资时代的机遇。在他的“搭搭班”里,既做实业公司,也做房地产之类。父亲从没有失手过。他仍然每天往返于翁垟和柳市之间,只是不再骑自行车,而是由司机每天接送上下班。仍然吃着更多的剩菜,信奉着一顿菜要分到几餐里的道理,仍然抽着十六块钱的烟。他也仍然视自己为壮年。他说自己在二十多岁就被人看成是中年,但到了六十多岁,还是中年。父亲的脸上鲜少老人斑,也没有皱纹,只是两鬓已起白发,动作稍显笨拙。而母亲则称,父亲的双手一直是笨拙有余的,理由是父亲即使与电器结缘四十年,换个灯泡手仍会抖。我们也会从父亲迟缓的动作里提醒他,是到了服老的时候了。父亲最忌讳把他看成是一个老人。他有时也会产生买几套名牌服饰的念头,当母亲为此数落他的时候,他还会露出腼腆的笑容。
岁月如常。也是在岁月如常中,父亲先是为我在乐清买了一套房子,接着又为哥哥在温州买了一套房子。哥哥的房子签合同时,父亲把我也叫了过去。这一年是2008年,父亲六十四岁。
我和哥哥都买了房子后,父亲回到了村里的老房子。至今,他在我们城里的家住的次数,合计不超过十次。他已经习惯了老房子的生活。他的身心都融入了这座老房子及周边的土地。他也习惯了在这座老房子里,和老朋友们谈天说地。他的老朋友总是一茬一茬地来。父亲是他们眼中无可争议的老好人。一有什么事,他们也喜欢找父亲商量。父亲在他们的推举下两度以最高票当选村老年协会的委员。但他的心态,仍然是“搭搭班”的。父亲其实只想做好这座老房子的一家之主。有一年,我和哥哥、姐姐商量,在乐清办分岁酒,也就是年夜饭。我开车去接父亲,父亲愣是不想来。他生气了,生的是没有责备声的闷气。吃完分岁酒就和母亲回家了。也只有母亲体会得到父亲生气的理由。她临走时撂下一句话:
“你爸是不想家里恁冷清。”
母亲口中的家特指那座老房子。我们再没有在乐清办过分岁酒。我们也习惯了每年的春节都在老家过。
4
2009年冬,父亲决定在老家的位置上,第三次砌新屋。次年春月,破土兴工。
对于这次砌新屋,父亲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独断力。他否决了我们诸多新潮的设想,从构架一直到装修,都是亲自决定。他向我们征询意见是象征性的,或者只是习惯性的。唯一谈得上“商量话商量讲”的是母亲。之后购买家具则完全交由母亲决定。主外主内,相得益彰。我们直到后来才发现这一点。哥哥告诉我,父亲和母亲是把它当成平生最后一件大事去做的,他们自己满意最重要。
父亲和母亲包揽了新宅从兴建到装修的大部分粗活。在一个月时间里,父亲瘦了八斤。从一摞一摞搬运家具开始,到一起搬运拆迁下来的碎砖碎瓦到后山,再到选购和搬运钢筋、水泥、沙子、“苍蝇头”,再到现浇养护,及至装修阶段的搬运木材、瓷砖、地板等,父亲都是亲力亲为。现浇养护时正值盛夏,父亲穿着雨衣,脸上满是汗水和池水,头发蓬松凌乱,眼神也因为疲惫而变得僵滞,看起来,倒像是在三十几年后又成了一个可怜的农民工。尽管父亲向来节省,但这一次,我总觉得他的节省多了一层特殊的意味。即使在砌二层楼时,父亲也从未感叹过辛苦和劳累。
八个月后,新宅上梁的时刻一直铭记在我们心里。那是农历庚寅年十一月廿四丑时一刻。
我和哥哥一家人前一天的下午就赶回老家,而老家又成了新宅。我特意带上照相机。一盏白炽灯和一对红烛的光亮使大堂充满温暖的色调。大门两侧,是大红的对联和灯笼。一根长杆靠在二楼窗户上,周身缠缚大红绒线,其上有糠筛米筛、镜子、布尺、万年青,也是张贴红色,寓意映红。母亲在摆放各色各样的祭品。父亲在梁木上规则地***青色和红色的绒线,象征青龙、红龙,以及一对风水瓶、一对榔兴、一对金元宝、一对红灯、两串橘子。他们之后为使猪嘴衔上猪尾费了一番功夫。父亲衔着烟掰开猪嘴,母亲使劲往里塞,二人说说笑笑。准备停当,离丑时一刻的涨潮还有很长时间,我们围坐在供奉祭品的大方桌周围聊天。自然地就谈起这是我们家第三次在这块土地上兴建房子了。从最初的石头屋到二层楼再到现在的六层楼。父亲也从青年走到中年再走到晚年。这偌大的三间六层楼房子,平素只住着父亲和母亲两个人。我说这样的铺张浪费违背了我们省吃俭用的家风。父亲则正色回答我:“这是要万古流传的。”
万古流传,乐清方言中的“万”发音短促,立刻承接“古”,整体的语调比普通话平和而内敛。这不是父亲第一次说出万古流传。一旦与父亲的交谈涉及土地或祖先,父亲便会常常用到这四个字。再也没有比这更加根深蒂固影响过父亲了。他一定要守着老宅并在年近七十时重建;每年大年三十都要亲自“照岁”(过年祭拜祖先的习俗),年夜饭也必定是先向祖宗敬酒三巡;每年清明都要带着家族的后辈上坟;新宅落成前为妥善安放先祖的香炉求教多位前辈;他如此重视我们的教育,及至如此期盼有一个孙子。父亲终究是一个农民。父亲处在一个变化的时代又亲历这个时代的变化。他抓住了这个时代赋予的诸多机会。作为乐清的第一代电器人,他为之付出了四十多年时光。但父亲又始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电器人。一个行业的成熟总是会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我们通常也只是羡慕和追逐塔尖的风光。而父亲让我把目光回落在更加庞大、默默无闻的塔基上。我也发现了更多像父亲一样默默无闻的塔基。他们从农业社会中走出来,从事过或正在从事着电器行业,骨子里却一直保存着一份农民的天性。父亲在电器行业的四十多年,秉承的也是守成、勤劳、敦厚、忍耐、节俭的农民品质。他的财富积累是缓慢的、平稳的,从未有过大起大落。由此,父亲愈发显得沉着和自信。
那天晚上,父亲还向我们念叨起与他有关的几座房子。寒夜的村庄静得出奇。父亲说得兴起,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母亲数落父亲自吹自擂。之后大木师傅和水泥师傅相继到来。我与哥哥抬着缠缚青龙和红龙的梁木走到六楼。在庄严的仪式里,我们紧张地站在梯凳上,把梁木连带一本皇历嵌入预先留出的梁穴里。鞭炮声随即响起。接着父亲点燃杉树刺,我和哥哥把茶叶米洒在燃烧的杉树刺上。一层一层,层层如此。回到一楼,母亲已经准备好寓意招财的香炉。父亲、哥哥和我各敬了三支香,一起将香炉端上六楼,置入墙格,又拜了三拜。
上梁至此礼成。父亲一只手搭在被火光映得通红的水泥墙上,神情凝重。我的眼前旋即闪过生活三十年的二层楼老宅拆除的瞬间。那一天,父亲也是一只手搭在邻居的墙上,神情凝重地抽着烟。
林晓哲,1980年生,浙江乐清人。中短篇小说见于《收获》《江南》《天涯》等。曾获《上海文学》短篇小说新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