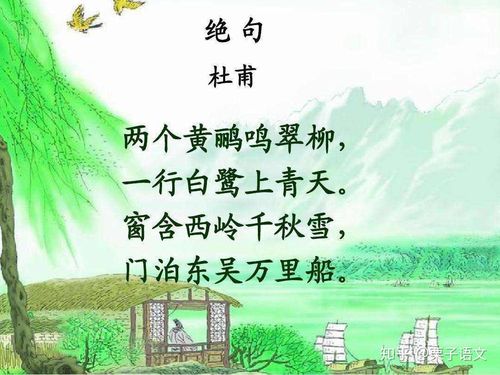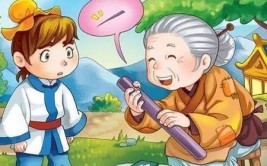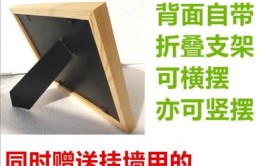关于此事,史书并无任何交代,历来诗评家也未曾着眼于此,故笔者此文只是在近些年论文的基础上进行尝试性的解答,多有臆测之处,而不敢妄称全备。
考察生平年谱,二人是时空可能有交集的机会有两次。
一次是开元十八年到开元十九年(730年—731年)此是李白初入长安之时;另一次是天宝元年到天宝三年(742年—744年)此是李白受诏入京、特受恩宠之时。
白天性好交游,这几年的长安生活,使李白结交了许多朋友,但却独独没有王维。
下面我将对此事进行尝试性解答:
一、开元十八年到开元十九年(730年—731年)
王维少时便以文章音律得名,十九岁时,得岐王与玉真公主的帮助,京兆府试,取得解头。
按一般的见解,既为状元,日后必定飞黄腾达。
但情况并非如此,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一些。
在开元八年(720年),也即王维中状元的次年,朝廷便明令“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王维早年结交的贵人对他便再无擢升之用。
开元九年(721年),王维任太乐丞,因“黄狮子”一案又被谪为司仓参军。
可以说,王维的仕途是高开低走,并不顺利。
在诗名上,王维彼时创作且流传下来的名作并不多,查《右丞年谱》可知,名作只有《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息夫人》等,支撑其诗名的《辋川集》等重要作品还未创作。
所谓“得名”,大约也只是因为音乐上的天赋。
再加上开元十八年李白入京,正值王维因痛失伉俪而沉沦在野之时。
王维与其妻特为情深,丧妻之后,“孤居三十年”。
此时正值王维情绪极为低落之时,很难萌发嘤嘤求友之念。
而李白此时正踌躇满志地入京,遍干诸侯以期展露雄才,对于政治地位不高、诗名也未显露的王维来说,李白很难会主动去结交这样的朋友。
再者,李白入长安,是寄食于玉真公主的别馆的。
这栋别馆距离王维住处长安百有余里,且环境十分恶劣,有两首《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可以为证,下举其一。
秋坐金张馆,繁阴昼不开。
空烟迷雨色,萧飒望中来。
翳翳昏垫苦,沈沈忧恨催。
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
吟咏思管乐,此人已成灰。
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
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
可见玉真公主并未善待他,此行李白是颇为不得意的,于是写了许多怀才不遇类型的诗。
“若无清风吹,香气味谁发”(《古风·孤兰生幽园》)、“当荣君不采,飘落欲何依”(《感遇·可叹东篱菊》)、“无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所以秋末李白便离开了长安,开始了游山玩水的“岐、邠之行”。
二、天宝元年到天宝三年(742年—744年)
天宝元年,在至交元丹丘(旧说吴筠举荐李白,误)与贵人玉真公主的帮助之下,李白受诏入京。
此行李白一开始是颇为风光的。
刚从泰山游玩回来的李白,饱览山河之气,秋时得诏入京,英气勃发,作《南陵别儿童入京》,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之句。
来到长安,得到唐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赐食于前,御手调羹”的恩宠,贺知章更是称其为“谪仙人”。
此时留下了许多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警世通言》中《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一章,高潮处便是这一时期的。
李白好结友,开元年间便有一个“竹溪六逸”的小团体。
来到长安,又有了“饮中八仙”的团体,且另外“七仙”如贺知章、王琎、左适之、崔宗之个个都是煊赫一时的名士。
同一时期李白结交的还有李龟年、卢象、独孤驸马等名流。
可以想见,当时李白交往的都是一流人物。
而此时王维呢?王维因为改元而从左补阙迁为库部郎中,然而这仍然只是一个小官。
与如今大红大紫的李白相比,实在冷清得很。
查《右丞年谱》,此时王维所作多是与朋友裴迪、苑咸、兄弟王缙的赠答。
这实在是两个阶级的交往团体,彼此不相往来是可以理解的。
王辉斌先生认为李白彼时极可能没听过王维之名,依我见不大可能。
王维年少成名,十九岁“赴京兆府试”便“举解头”,此事虽给王维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但对其知名度的提升应是无疑的。
维工草隶,善画,名盛于开元、天宝间,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
(《新唐书·王维传》)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作乱,因为安禄山“素知其才”才任命王维作给事中。
若当时无一定的社会影响,想必不会声闻于安禄山之耳。
《唐朝名画录》中记载王维、王缙兄弟并以科名文学,冠绝当世。
故时称“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诗”;苑咸酬答王维诗诗题称“当代诗匠”;以上诸例,皆可证王维当时已诗名颇显了。
二人绝不相交,怕还是以二人之地位差距与性格原因为主。
三、性格与信仰差异
太白自24岁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有“已将书剑许明时”之句足见其初出毛犊的勃勃雄心。
但遗憾的是“遍干诸侯”,却毫无结果。
别匡山(唐·李白)
晓峰如画碧参差,藤影风摇拂槛垂。
野径来多将犬伴,人间归晚带樵随。
看云客倚啼猿树,洗钵僧临失鹤池。
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
终于在开元十八年(730年,白30岁)来到唐王朝的首都长安,期望于京城一展抱负。
白素来自负奇才,却不能走寻常读书人发迹的科举之路,原因在于其社会地位低下,父亲是个商人,唐人科举规则是“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
此行又有干谒奇文《上安州裴长史书》一篇,颇能见白之心迹。
他说自己是“本家金陵,世为右姓。
”右姓,就是豪门贵姓。
明明是最低下的商人出身,为什么非要说自己是右姓呢?如果这一条是唐人一贯的自吹自擂的传统,那么他日后还有诗云“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
”一会儿说自己是金陵的豪门大姓,一会儿又说自己是陇西的武将世家,这是为什么呢?依我见,恐怕还是为了遮掩自己不太光彩的商人出身吧。
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窥探出一代诗仙李白自负的背后,其实是暗藏着自卑的。
第一次入京,他心雄万夫却一无所获,只落得几个月后黯然离京。
第二次奉诏入京却只获得个虚职,沦为太平天子的掌上玩物,最后赐金放还。
一个人对自己的才能过于自负、对自己的期望预设又过高,那么当他碰壁于冷酷现实时,不免对自己产生怀疑、放大自卑的心理。
但越自卑就越要自负,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要说不屑于得到。
但李白有自己的道德支拄,他是绝不肯苟合浊流的,这使他可以昂首说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出身、时运、性格使他更加倾向于“道家”一路。
他的理想进可以出仕、进不可得,退可以求仙,可以“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过上自由随心的生活。
而王维和李白不同,他性格偏向懦弱,没有李白的棱角与强项。
他很得诗人宰相张九龄的赏识,在张九龄的运作下,王维才擢升到右拾遗的位置。
但后来张九龄在与李林甫的政治斗争失败后,王维并没有站出来为张九龄说话,只是写诗宽慰他。
但一方面又接着写诗阿谀新宰相李林甫,不能说王维心底就一定尊崇李林甫,但他的忍尤攘诟以保持官位,在士林看来显然是缺乏气节的表现。
天宝十五年,安禄山兵入长安,王维“扈从不及,为贼所获”。
安禄山授以位置时,他也是忍气吞声地接受。
安史之乱后,即使士林对王维没有表示鄙夷之意,恐怕王维自己也会自生厌恶吧。
仕途上的污点、性格上的缺点,再加上一个信佛的家庭环境,使得王维更倾向于具有“忏悔意味”的佛教。
一仙一佛,一放一敛,一刚一柔,二人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想象,即使他们有数年同居长安的生活,互不相见或者互不打扰也应当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结言
李白、王维是盛唐诗史的两座丰碑。
徐增《而庵诗话》“诗总不离乎才也。
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
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诘。
”
但无论“天才”还是“人才”,首先都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所应有的心理我们都可以拿来猜测与分析。
本文便是立足于一些基础史料和诗歌文本,对李、王二人不相交往的原因做出的一个尝试性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