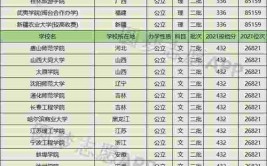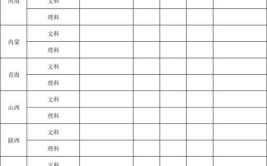蠡湖是太湖伸入无锡的内湖,范蠡与西施曾泛舟于此。湖上的珍宝舫是用餐和赏景的最佳去处。
四月的太湖边,一簇簇灿如散金的油菜花开得正尽兴,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不雨而润的气息。我知道,我的太湖又迎来了新的轮回。再过些时候,鲜美的莼菜就该上市了。我一直把莼菜当作春天的信号,那种黏黏滑滑的口感,鲜而不腻。虽然吃过无数次莼菜,不管是“银鱼莼菜羹”还是“芙蓉莼菜”,但我依旧很难总结它奇妙的口感。这一点,古人也有同感,因为《耕余录》就形容它“比亦无得当者,惟花中之兰,果之荔枝,差堪作配”。
莼菜一直被视为菜中精品,《齐民要术》中称“诸菜中莼为第一”。“银鱼莼菜羹”将太湖两大特产最好地组合在一起。

不管在家里,还是在豪华酒店中,莼菜的烹饪方法无非是配荤炒、或素食、或氽汤,还有将其做馅的,此外并无更多招数。太湖边上的吴县璜泾有一道“昂刺滚莼菜”,用金黄色的小昂刺鱼和淡绿的莼菜搭配,算是“四美羹”的简易版;而在今天,最地道的莼菜吃法肯定是“银鱼莼菜羹”。五六月时,洁白如玉的太湖银鱼进入产期,彼时正是捕捞的好时候,也正当“春莼菜”的采摘季。无鳞无骨、通体鲜嫩的银鱼和柔如呼吸的莼菜一起烹饪,依然必须是用勺取食的羹汤,清白明丽,口感稠密如锦缎,滋味丰富如茶韵。
在大量春夏蔬菜上市之前,街头最常见的是这种黄心菜。
不过我最期待的,还是李渔“终极版”的四美羹:“陆之蕈,水之莼,皆清虚妙物也。予尝以二物作羹,和以蟹之黄,鱼之肋,名曰‘四美羹’”。用蕈、莼菜、蟹黄和鱼肚做菜,是把清鲜滑嫩做到了极致,口舌之间还在不舍这清丽妙物,它们却已经直接滑落到了肚子里。我还没有在哪家餐厅里吃到过这道菜,据说有些文雅之士兴起之时会在家中研究它的做法。这也是我喜爱太湖的地方,它既展现了平民质朴简单的本能,也反映了精英审美的热情,这种冲突与融合怕是别处难以常见的。也正是如此,虽然太湖吃食在理论体系和烹饪方法上都并没有形成纯粹单一的小宇宙,但太湖菜作为传统美食版图的一隅,哪怕是一箪食、一瓢饮,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气”,寻味中国自然不能错过这里。
太湖很大,有两千多平方公里,这个中国第三大淡水湖里有三样东西最为人熟知,那就是“太湖三白”——银鱼、白鱼和白虾,它们和莼菜一样都是文人的心水、诗歌里的常客。白鱼和白虾在农历五月至七月间进入产量高峰期,其烹饪方法以蒸煮为要,追求味道的本真。蒸煮方式在太湖一带十分常见,它是水与火调和的艺术,最能得清虚淡雅的妙处,也最能减轻肠胃的负担。
鳜鱼生性凶猛,但肉质鲜美,又有补胃之功效,深受食客喜爱。
太湖醉虾。
虽然“三白”在太湖一带的大小餐厅中都是主角,但真正野生的并不多见。就像光福镇的一位老渔民所言,他们捕捞的白鱼出手价通常一斤要六十元左右,到了餐厅翻一番的价格也属正常。如果是几十元的白鱼,毫无疑问是养殖的。所以吃一顿地道的太湖鱼鲜,价格很难平易近人。但说回来,太湖美在太湖水,也美在太湖里的好食材,那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味道。西晋张翰,一个坐言起行的吃货,是为了家乡的两道菜,挂印而去,变成了浪漫文人。莼菜和鲈鱼也变成了思乡的图腾,这两道成为文化符号的名菜正凸显了太湖美食的典型滋味:斯文清淡。
“水八仙”中的慈姑个大质糯,常红烧或与鸡汤同炖,可清热润肺。
菜花地附近的水塘是塘鲤鱼的最佳生长地,这种鱼的鱼骨少、易剔除,肉质洁白细嫩,与鸡蛋同炖,最能凸显两种食材的最佳状态。
小时候,我在太湖边玩耍,一望无际的太湖总是惹得我莫名惆怅。无论是阳光下的波光粼粼,还是阴雨天里的沉默灰暗,我都觉得太湖深不可测,大到我无法控制,仿佛时间和空间都到此为止。湖的那边到底是什么模样?也有我这样的人在湖边感叹吗?
我出生在苏州东山,这里良田绵延,茶树层叠,鱼池更是星罗棋布,除了“太湖三白”和莼菜之外,太湖里还有多达上百的不同鱼种。太湖于我,就是南方文化的母亲湖,它连带江浙两省,沿岸有苏州、无锡、常州和湖州四座名城,自古以来人文荟萃。虽然苏州和无锡关于“太湖到底属于哪个城市”争执已久,但两地人对于太湖的情感是一样的,远在诗人们的扁舟花船之前,湖面上纵横往来的多是“一舱点灯三舱亮”的渔船。渔民和生活在太湖附近的人才是最了解和最爱惜太湖的,湖水就是我们的生命,干净健康的湖水滋养了一代代的太湖人。
在苏州临湖镇,我遇到了身强体壮的陈八斤,他正拎着一条大鳜鱼走过来:“这条鱼在湖里已经生活了十多年。”这就是当地人对太湖情感的一种表达,他们世居岸上,鱼则在水里繁衍,岁月在中间调和,鱼和人都依靠太湖的恩泽,是一种平行的生活方式。虽然这条重九斤,大概值一千多元的野生鳜鱼最后难逃被红烧的命运,但陈八斤的言语里还是透露出对它的不舍。
肥大的野生鳜鱼让陈八斤欣喜不已。
水上和水边的生活到底不都是诗意的,太湖渔民曾一边唱着“鱼眼乌珠不眨,渔民一世不发”的歌谣,一边把包括“三白”在内的上好鱼珍销往金字塔的顶端。虽然从前的渔民很少吃到上好的水产,但是他们烹饪起好食材来,往往别出机杼,和我们所熟知的清鲜淡爽的格调大异其趣,成为太湖美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三代以捕鱼为生的陈八斤,就在自己的“太湖生态渔村”推行用渔家秘方来烧制的各种湖鲜。他们做的红烧鳜鱼,酱汁醇厚,鱼肉清鲜,混在一起又有难得的野趣,令人惊艳。我在苏州的“香宫”餐厅吃过另外一种味道的“秧草太湖小鳜鱼”,因为秧草的清新,鳜鱼即使红烧也毫不油腻,反而别有一番风味。
银鱼无鳞、无刺、无腥味,肉质细嫩,可做羹汤,也可酥炸。
农家院和高档餐厅,这是美食消费的两头,虽然形式不同,但他们拼的却一样——用杯盏里的安静,做出太湖里流转的活力。“太湖桂花藕”、“生呛太湖虾”、“上汤太湖白鱼大鱼丸”、“鸡头米湖虾仁”和“姑苏江南水八仙”等,哪一个不是念着朗朗上口,想着就让人垂涎三尺。说到“水八仙”,古时的苏州葑门外溪流清映,地势低洼,遍布泥田,最宜生长茭白等“水八仙”(“葑”指的是茭白根),此地的茭白品质堪称全国翘楚。茭白作为“水八仙”的当头一炮,鲜嫩爽利,荤素两相宜,以茭白为代表的水培蔬菜也正是太湖美食的重要分蘖。水培蔬菜卖的是新鲜,出水看泥,越水灵越好。要水灵一定要去我最爱的葑门早市,那是一条狭窄的长巷,本地人操着暖糯中透着精明的吴侬软语,挑选着最中意的食材。这里有很多周边的渔民和农民,分辨起来非常容易,因为他们的面前通常只摆着两个竹筐,放着同样的食材,要么是青虾,要么是塘鲤鱼,要么是土鸡蛋,要么黄心菜。他们靠着墙边坐着,安静而专注,好像卖的不是食材,而是生活的正果。
“ 香宫”的鸡头米湖虾仁味道清甜可口。
春天的太湖是最美的,一切都生机勃发。从范蠡开始,太湖地区巨商大贾辈出,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再加上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太湖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旅游胜地。如今欣赏太湖可以沿着环太湖路一直前行。湖边的船只星罗棋布,村庄淳朴安静,突然冒出来的竹林也像妙手偶得,这些都让人备感亲切,谁看见了,都觉得自己是乡亲,而非过客。从苏州市内到东山、西山,先看吴中建筑群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陆巷古村,登“太湖第一峰”缥缈峰后,还能在光福镇看看壮观的渔船,这时你肯定如我一样期待一场船菜之约了。
桂花年糕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太湖船菜本来是游船、画舫上待客的筵席,船菜的主食材当然是太湖的水产和禽类,一般是在岸上的店里做初步加工,到了水上之后,再继续烹为成品。船菜相较于岸上的菜肴,更加讲究新鲜,以“味真和应季”为上品,力求让人的眼睛和味觉同步感受太湖的光阴变化。不过如今的太湖船菜,大多已经失去传统韵致,变成了景点门票;这样的一场筵席吃下来,味道往往复杂多变,不够尽兴。行游太湖,如经典船菜那样丰满的美食文化,已经不可再得。今天的太湖,吞吐着水系内的172条河流,哺育人口无数,它要不断和日益变化的水情和人心作对抗。在这场对抗中,有些东西被幸运地保留了下来,比如陈八斤的鳜鱼,又有些东西却奔流到海不复回,比如船菜。
太湖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盛产“太湖三白”和太湖蟹等。
春季的莼菜水青、银鱼洁白;夏天的红菱艳丽,荷花有银白或粉嫩;秋天,菊花和蟹黄比着耀眼的金;冬天又有腊梅满坡。四季的变换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美食,眼睛和肠胃从来不会感到单调,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生活,有美妙的生之愉悦。
餐厅推荐
北京万达索菲特一品淮扬
餐厅拥有4间专属包间和一个开放式用餐区,由杰出的淮扬菜系烹饪大师蒋应荣主理。代表菜品有 “ 烧汁银鳕鱼”、 “ 清炖狮子头”、“银鱼蒸蛋”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万达广场C座
电话:010-85996666
苏州香格里拉大酒店香宫
每一家香宫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食材,地道正宗的季节性菜肴一定不能错过。中餐行政总厨徐国章拥有20年的烹饪经验,擅长制作淮扬菜,热衷于寻找不同食材。“太湖三白”和“水八仙”在他的菜单中均有不俗表现。
地址:苏州市苏州香格里拉大酒店内2~3层
电话:0512-68080168-23
价格:约¥200/人
苏州太湖生态渔村
一家集养殖、垂钓、休闲、住宿为一体的新兴太湖度假村,湖鲜是这里的最大特色,这里的太湖大闸蟹也品质出众,值得一试。
地址:苏州吴中区临湖镇生态渔村
电话:0512-66292826
价格:约¥180/人
无锡太湖珍宝舫
太湖边的锡菜老字号,环境十分幽静,湖鲜烹饪有无锡特色。
地址:无锡市无锡滨湖区环湖路1号
电话:0510-85103784
价格:约¥200/人
.....................
文章来源
《悦游Condé Nast Traveler》往期
food & drink栏目
摄影/曹勇、LT
撰文/LT、吴春
原文编辑/李甜
微信编辑/Steven
悦游原创文章,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
飞机上那些“奇怪”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