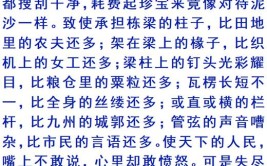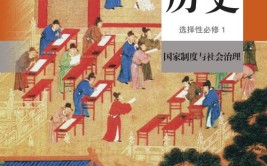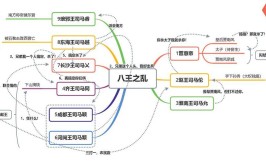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伊朗族及其文明是不能绕开的话题。伊朗族的构成部分较为复杂,包括波斯人、米代人和大多数古伊朗的其他民族。严格来说,这是印度—伊朗人或称为“雅利安人”大家庭的一个分支。而雅利安人本身是印度—欧罗巴民族中的一部分,后来由于一些原因定居伊朗。具体定居时间,我们无从知晓。早在公元前14世纪时,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西北部,就生活着许多米坦尼人。他们的国王便有印度—伊朗式的称号,整体族群也敬奉着印度—伊朗的神祇。
\r\r在语言方面,原始的伊朗语言和梵语颇有渊源。查阅史料,我们能知道伊朗语有两种方言形式。一种被称为“老波斯语”,是波斯本部法尔斯的语言。另一种则是“真德语”,既是米代即米地亚的方言,还是拜火教圣书即《阿吠斯陀》所使用的语言。后来在生产发展中还出现了一种伊朗语言,即帕拉维语或派勒维语,是帕尔提亚人和萨珊王朝的人们使用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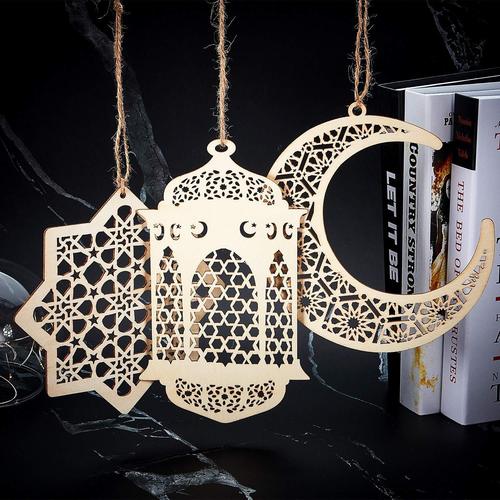
在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伊朗族人,应是居住在今伊拉克—夷·阿杰米地区的米代人。公元前612年,米代人的君主赛阿克萨利斯攻克了尼尼微。随着新政权的兴起,亚述人的领土变得四分五裂,大多落入米代人及其盟友巴比伦人的手中。经过两方势力的博弈,米代人占领了亚述本土,巴比伦人则占领了迦勒底和叙利亚。历史发展永恒的主旋律,就是政权的更迭翻覆。公元前550年或前549年,另一支强大的伊朗族波斯人击溃了米代人建立的帝国。这支强悍的势力在其主君居鲁士的带领下,继续蚕食米代人的领土及其藩属范围的土地。野心一旦燃起,便不会轻易熄灭。公元前546年,这支势力又吞并了小亚细亚地区的吕底亚王国。随后在公元前545—前539年,居鲁士又将势力范围扩张到印度河东部的伊朗地区。最后在公元前538年,他率兵攻克了巴比伦帝国即迦勒底和叙利亚地区。战争如同一把举世无双的利刃,被君王们拿在手中开疆拓土。经过多年的杀伐决战,阿契美尼德王朝终于建立起来,直到公元前330年迎来覆灭。公元前525年,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继续征伐,顺利征服了埃及。
\r\r而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实力一度滑坡,甚至开始走向衰微。但王族后裔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1—前486年)即位后,重新整顿朝纲,挽救了国家危局。与此同时,大流士一世及其后代的野心不止于此,他们还将目光转向了希腊的领土。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对希腊的征伐都以失败告终。就连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一世(公元前486—前465年),也同样铩羽而归。公元前第5世纪末、前第4世纪初时,希腊政权所面临的威胁愈加减少,只在经济和外交方面受到影响。这一时期,阿契美尼德王朝[1]的君主多以阿塔薛西斯或大流士为名。到了大流士三世时,这个王朝逐渐走向末日,被马其顿王朝的统治者亚历山大大帝所灭亡。而后,波斯帝国也没能躲过大帝的征伐,于公元前334—前324年间彻底覆亡。
\r\r在古代世界的诸多民族中,波斯人是最为高尚的族群之一。尤其在他们历史发展的第一阶段,充满了荣誉感和侠义主义,富有人性的光辉色彩。这种精神文化如同汩汩细流,能够给人们极大的宽慰。那些经历过亚述—巴比伦或者布匿克政权统治的人们,更能在邪恶、野蛮和残忍的强烈对比下,感受到波斯人的高尚精神。从波斯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起,我们就能感觉出他们身上的亲切感。例如,希腊人在与波斯人互相争斗后,便将其视作值得尊重的对手,而非对待普通属国一般居高临下。这种发自内心的敬意,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希罗多德是希腊著名的希腊史历史学家,他曾写道:“受到教育的波斯青年,都懂得三件事:骑马、射箭和永远真挚诚实。”
\r\r在伊朗人和印度人彻底划分界限之前,他们共同属于印度—伊朗民族。这个民族所信仰的原始宗教较为特别,主要供奉着两类主神。一种名叫“提婆”,又称“天神”,其寓意是青天上的神;另一种名为“阿修罗”或“阿胡拉”,即侧重道德方面的“真主”,纯属自然方面的成分较少。随着这两个民族的分裂,人们对于这两种神祇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印度人的变化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将“提婆”升格至“上帝”的高度;二是将阿修罗的地位贬低为神祇的敌人,如同希腊神话中的“泰坦”一般,之后则干脆视之为魔鬼。相对地,伊朗人的变化也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将“提婆”变为魔鬼,又称为“提夫”;二是将“阿修罗”视作唯一的真神。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到了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伊朗人的信仰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大流士一世镌刻在岩石上的铭文内容,我们能清楚看出这一点。在这一时期,阿修罗其中之一的“阿胡拉·玛兹达”[2]已经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神。这位原本只是象征着智慧的神祇,开始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此时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已然忽视了其他神祇的存在,王室成员只信奉“阿胡拉·玛兹达”。这样一来,王朝距离一神教就剩咫尺之遥。信众们强烈的崇拜情绪,往往会通过一系列仪式表现出来。比如在露天祭坛上点燃圣火,这种火焰会被称为“阿塔尔”。在波塞波利斯[3]地区,研究人员发掘出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贵族陵墓,在墙壁的高浮雕上发现许多图案。这些别致的图案仔细刻画了点燃圣火的仪式,是我们研究史实最为有力的证据。在神秘的仪式上,国王端庄地站立在祭坛之前,一个长着双翼的神灵形象同时出现在上方。有猜想认为,这个神灵形象是阿胡拉·玛兹达,或者是国王的保护神即“弗莱瓦什”。相对比之下,印度—伊朗民族所信奉的另一大神祇米特拉却很少出现。在原本的宗教中,米特拉是“信约之神”,代表着约束众人言行的含义,后来变成了太阳神。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风俗中,人们普遍有埋葬死者的传统习惯。与这种风俗习惯并存的,是一个由僧侣组成的教派或阶级。这个教派名叫麦吉教,常被希罗多德提起。根据他描述的种种迹象,我们不难推测出麦吉教就是左拉图斯特拉或琐罗亚斯德的玛兹达教,又称“拜火教”。
\r\r对于琐罗亚斯德的研究,到今天还在继续。由于史料有限,他的生存年代很难精准确定下来,大概时间约在公元前第7世纪时期。按照传统的说法,琐罗亚斯德生于米代,在20岁时开始遁世隐居。而后到了33岁,他开始向世人传播自己的教义。在琐罗亚斯德的辛勤努力下,一位名叫维什塔斯帕的王子被成功教化。而后,他还曾远行到巴克妥利亚地区。77岁那年,他在蛮族入侵引发的战乱中丧生。琐罗亚斯德还撰写了圣书《阿吠斯陀》,其中最古老部分“伽塔(圣歌)”的作成时间,似乎正是公元前7世纪——这位教主实际生存的年代。而这部圣书的其他部分,则在较晚时期才成书。琐罗亚斯德曾在“伽塔”(圣歌)中说,他的使命是来净化宗教。换言之,他的教义从一开始就更加注重精神方面的教化,以二元论为本原的基础。具体来说,这种精神的内涵一方面有阿胡拉·玛兹达,代表光明和善良的本原,被信奉为神明。相对应的另一方面,有安哥拉·曼纽,代表着黑暗和罪恶的本原,如同玛兹达教中的撒旦一般。这两种力量分别造出世界上的一切善良和一切邪恶,互相对应与制衡。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神祇与阿胡拉·玛兹达所并存。这些神明是将高洁品德人格化之后的产物,他们的地位相当于基督教中的天使。地位较高的神祇是六位“阿美沙·斯朋陀”,代表着“圣不朽者”,是种种抽象概念和基本道德的人格化,比如,代表着善良思想的“沃胡·玛诺”,代表着高尚德行的“阿沙·瓦希什陀”。在这六位“阿美沙·斯朋陀”之下,还有无数被称为“耶泽陀”的圣灵。其中最重要的是火神“阿塔尔”,被称为“阿胡拉·玛兹达之子”,常排在第一位。在玛兹达教中,“阿塔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圣火祭坛就是为了供奉他而设的。在“耶泽陀”中,与火神相对应的还有水神“阿波”,也有其神圣的地位和寓意。除此之外还有日神“赫瓦尔”,代表着光的威力,是前面所提到的信约之神“米特拉”的仆从。传奇的是,供奉祭拜米特拉的教派还将这位神祇传播到了希腊—罗马世界。“弗莱瓦什”和“维利特拉格纳”也属于善良神祇“耶泽陀”群体,各自都有神圣的意义。前者既是保护神,又代表着灵魂的本质,后者则是胜利之神。与这群善良神明相对应的,则是由安哥拉·曼纽所创造出的代表邪恶的神祇。其中的“提婆”即“达依瓦”,与许多其他印度教中的神明一样,从前有着崇高的地位,后来却被贬低为恶魔或者魔王。往昔代表着圣洁与光辉的神明,渐渐变得与“德鲁吉”和“派丽佳”为伍。要知道这两者分别代表着厉鬼和女妖,都是为信教者所厌恶的。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本质上都是善与恶的彼此斗争,以及互相流转与制衡的过程。在研究宗教的过程中,更能发现和验证这一点。玛兹达教徒们虔诚地相信,在人死后他们的灵魂是不灭的,会经过一道“审判桥”,决定此后去向。一般而言,过桥的灵魂会被神明审核生前的种种言行举止,或是升往“圣歌之乡”享受快乐,或是被发配到地狱和“德鲁吉”作伴。在玛兹达教的经文结尾,也有对世界万物命运的乐观设想。在时间走向终结的时候,会有奇特的人物“瑞希安特”出世。他是琐罗亚斯德的儿子,一直待在父亲身边,就像基督教中的“弥赛亚”一样,负责主持死者复活后的最后审判。世界万物走向尽头时,大地弥漫着一片汪洋似的熔金。在一片寂灭之象中,最后的审判就此开始,毁灭包括安哥拉·曼纽在内的一切恶类。这个时刻,所有善类终于战胜了恶,将会得救而后走向光明与极乐。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习俗中,人们会将死者埋葬。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正统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们的处理方式则完全相反。他们崇拜自然界如火、水、地等元素,不愿意让尸体污染了它们的纯净。所以,琐罗亚斯德教徒们会选择曝露死者的尸体。从这种细节的对比中,我们能够看出宗教的变迁与发展。具体来说,在萨珊王朝时的玛兹达教极具影响力,一度成为波斯国教。但到了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它的地位大幅下降,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教派。
\r\r君主国家因其统治理念的专制色彩,常具有等级森严、规矩严苛的特点。但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社会文化充满了开明包容的气象,在组织观念、治理人才和宗教等方面,都表现出了兼收并蓄、开放自由的风气。大流士一世在位时勤勉于政事,认真设计了波斯帝国行政机构的规划格局。他将自己统治的广袤领土,按照一定标准划分成整齐的小块,共约二十个行政区或者州郡。在每一个区都设有三位长官,分别是州长、皇家秘书和驻防军司令官。其中,州长负责处理民间事务,皇家秘书掌管与文牍有关的一切事宜,司令官则管辖着驻守当地的军队。这三位长官各司其职,由巡按统一监管。顾名思义,巡按的主要职责便是定期巡查各地方的行政状况。整体看来,这样的统治机制主要是按照两种原则设计的。第一是中央集权的思想,这在当时是很引人注目的;第二是分化地方官员的权力,以互相制衡的方式防止任意一方独大揽权,最大程度保证政局的稳固。
\r\r同时我们也要清楚,这种集中化并不代表着要将其他民族的个性全部磨灭和抹杀。相反,阿契美尼德王朝治下的其他各民族,都受到了优厚的待遇。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一样,波斯人始终信奉自由主义,就算成为东方世界的霸主,也依然心存仁念。他们仍会允许辖区内的其他民族保持精神独立,不断发展固有的文明。这样宽厚的心态,直接促使不同民族间的文明并肩前进。就连在敏感的宗教信仰方面,波斯人都未曾强行干预,一直抱着接纳容忍的态度。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亚述人。他们不仅要征服其他民族,还要用最严酷的手段改造敌人的信仰,即对外族人的“上帝”宣战。在亚述人的信仰中,本族的大神亚述和伊什塔尔同样所向披靡,不仅俘虏了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还打败了泰尔的贝阿尔、巴比伦的马尔都克、苏萨的苏西纳克和底比斯的阿蒙等神明。
\r\r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人则完全不同,从一开始便抱着兼收并蓄、谦逊仁爱的态度。他们对信仰充满了克制和理性,没有过分的狂热。比如,那时的波斯人从未将本族信奉的阿胡拉·玛兹达的地位提升到至高无上,也没有故意贬低赛姆人或埃及人所信仰的神明。到后来的萨珊王朝,波斯人才开始对玛兹达教无比狂热,与整个西方全然分裂开来。这样截然不同的政策,必然会取得完全相反的效果。这一点我们能从犹太人身上得到验证,特别是从他们对待征服者们的不同态度上。对于那些用铁血手段征战四方的民族,如埃及、亚述、迦勒底和后来的塞琉西与罗马的统治者们,犹太人充满了怨愤与不满,用种种诅咒来发泄胸中怒意。可是对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诸位君王们,犹太人却心悦诚服,甘愿承认他们是真正的主人。这种臣服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表现在犹太民族文化的许多细节中。比如,犹太人将居鲁士美化成了一位民族英雄,还让本族女子以斯帖登上《圣徒传》中的亚哈随鲁王的宝座。诸多细节汇总起来,我们能发觉这种判断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虽然阿契美尼德王朝是一个典型的君主制国家,也有专制主义色彩,难免会受到蠢笨拙陋且反复无常的君王影响。但是这些在宫廷中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并没有在政治层面造成巨大影响,动摇其稳固的根基。其后果远不如恺撒时代那样惨烈,没有出现血染罗马的惨剧。某一位大流士君王或者阿塔薛西斯王的个人行为,并不会阻碍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正常运转,也不会妨碍政府的福利设施。就像尼禄暴君虽然疯狂无道,却并不影响罗马人的和美生活。
\r\r亚述帝国建立后,统治者用严酷手段保持政局稳定,对被征服的民众横征暴敛。但是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君王用合理、正规且固定的税收制度来治理国家。除此之外,他还在帝国内部建立了发达的交通网。不管是从小亚细亚到埃及,还是从叙利亚到外乌浒河地区,都有通达的道路和驿站。为了保证其正常运转,政府还花费人力物力慎重维护着。因为社会环境的和平安宁,人们也打消了征战的心思。古代社会中常见的民族与民族间、人与人之间和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战争忽然销声匿迹,反而被一片祥和所取代。就像是西方世界的“罗马太平盛世”一般,阿契美尼德王朝也营造了东方世界的盛世。在两个世纪里,这个祥和的盛世一直存在于,从高加索山脉到阿拉伯沙漠、从博斯布鲁斯海峡和西里内伊卡到印度河的整个东方。与过去充满战乱和杀伐的时代相比,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在西方世界中,希腊时代之后的各城邦分崩离析,罗马帝国建立后又恢复了盛世祥和。而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人做出的功绩,完全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r\r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波斯人时,不应该仅仅把他们当作与希腊人对抗的“野蛮人”,还要考虑他们对人类发展做出的贡献。在战争和文化上波斯人略逊一筹,但这个民族建立的功业也是值得歌颂的。毕竟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相比,大部分民族都没有取得足够高度的文明成果。不管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不管是日耳曼人还是拉丁人,放在这样的天平上都会显得相形见绌。但是仔细研究就能发现,这些所谓的“蛮族人”或“未开化的人”,都没有辜负自身的使命。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波斯人和罗马人都是古代时期少有的民族,特别是能够长久地维持一个伟大帝国运行,这样的成就实属罕见,就连希腊人也没能做到。虽然在后世人眼中,希腊人充满了智慧和自由的光辉特质,但是没能保证宏大政局的稳固和长久。反观那个时期的波斯人,在建立中东霸业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成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政权。这个统一有序的政府运行平稳,还实施了诸多充满仁义色彩的政治举措。而在这广袤无垠的土地上,此前的人们都在赛姆族人的统治下,充满了仇恨、分裂和暴行。对比之下,我们便能发觉波斯人的贡献与成就。
\r\r在世界文明宝库中,米代—波斯文明是东方世界的璀璨明珠之一,散发着最为辉煌的光芒。希腊人对于苏萨和波塞波利斯的荣华十分向往,常常不厌其烦地赞扬这些文明。在现当代,人们发掘出了彩釉炼瓦浮雕的“射手”“众神”等作品,更加证实了那些时代的繁华与文明程度之高。如果追根溯源,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艺术的根源就在于伟大的亚述—巴比伦传统。就像希腊艺术对罗马艺术的影响一样,迦勒底—亚述艺术对波斯艺术的影响同样巨大且深远。这种影响力体现在波斯文明的方方面面,比如人们普遍使用的文字。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人一开始就采用了楔形文字,并且在之后进行简化。此前数目众多的符号,逐渐减少到只剩下36个。而且,那时的铭文作品,不管是单独运用老波斯语,还是常见的运用三种语言(老波斯语、伊拉姆—安赞尼特语和迦勒底语)的内容,都是用楔形文字刻画而成的。论及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物质文明,诸位君王所用的王室装饰可作为范例研究。这些装饰设计的精髓,完全继承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古王国文明的风格。王朝的君王住所,也选定在迦勒底—伊拉姆领土内的苏萨地区。除了道德的因素,单从文明的扩张与征服来看,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过程。米代人攻克了尼尼微,波斯人攻克了巴比伦,就像是古代迦勒底—亚述文明征服了伊朗一样。
\r\r \r\r□波塞波利斯之浅浮雕
\r\r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艺术\r\r任何艺术的发展,都不能脱离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艺术中,不仅有对前一时期古老文明的继承,还有在此基础上全面的创新与改革。这种艺术创新首先体现在了建筑物方面,如建造在石料结构上的王室宫殿,完全颠覆了亚述文明中的旧有建筑构造。经历了几千年的风吹雨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宫室建筑仍然保存完整。在此之前,亚述建筑物常以砖块搭建台基,外层覆盖石材,从此来容纳表面的浮雕。除了对建筑材料的革新之外,阿契美尼德王朝人还效仿了埃及文明中的设计风格。他们借鉴了石柱的元素,并将它广泛应用在宫室建筑物中。在萨尔恭王朝的宫殿设计中,圆柱只是一种装饰物。而到了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这种圆柱的地位已然大大提升,成为建筑物主要的构成部分。这种设计来自卡尔纳克和卢克索,在设计柱头时采用了典型的亚述风格。我们仔细观察圆柱上所刻画的图案,其主要题材与萨尔恭王朝时期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由两个互相背对着的牡牛的上半身组成的图案。在坟墓设计方面,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艺术家们也普遍借鉴了埃及文明中的相关设计。值得注意的是,据萨尔教授所说,这些艺术家们也会借鉴波斯的石椁形式,比如在玛什哈德—夷·木尔伽布地区发现的居鲁士的小型丘冢。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君王陵墓都是在半山腰开凿而成的,在陵墓正面的石壁上还有雕刻装饰。从这几处细节,我们很快就能联想到埃及坟墓的入口处设计。当然,这种借鉴并非全盘吸收。那些石壁上的装饰画题材大多是伊朗式样的,比如拜火坛和阿胡拉·玛兹达的光轮等。
\r\r \r\r□苏萨之柱头
\r\r在迦勒底—亚述文明中,纪念物的设计初衷大多带有宗教色彩,与某些宗教目的有关。但是在伊朗,袄教信奉虚空抽象的唯灵主义,认为人们建造神庙是受到外教异端污染的结果。所以为了保证宗教信仰的纯洁性,建筑物不能作信众膜拜之用,而仅仅是为了君王统治而服务。因此,在波塞波利斯和苏萨两个地区,挖掘出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建筑物遗址,都是宫殿而非神庙。
\r\r波塞波利斯卫城的装饰与设计可以说是极具特色。这座城池的台基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丘壑,有106级台阶可供人们向上攀登。台阶踏道的两侧,有用薄浮雕装饰的石壁。这些浮雕的题材大多是人物,比如战士、扈从和纳贡的王公等。远远望去,仿佛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在顺着台阶攀登一样。一直向上走到这条道路的尽头,能看到薛西斯王门阙,穿过后继续向前能看到一个极大的平台。在这块平台上,有一条西北至东南方向的直线。我们顺着这条直线,能看到的分别是薛西斯柱殿、大流士宫、薛西斯宫和阿塔薛西斯三世所建的宫殿。顾名思义,薛西斯柱殿以殿中的72根圆柱闻名,这些粗壮的柱子每根都高达80英尺。相较之下,大流士宫殿显得规模较小,而薛西斯宫则更加巨大。在这一系列的宫殿建筑物背后,即东北方向,有第二块平台,比此前的平台高出足足十英尺。第二块平台上屹立着“百柱大殿”,颇有底比斯柱殿的恢宏气势。据萨尔教授所说,这片建筑物是大流士受到底比斯柱殿的启发建造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柱廊及上面的薄浮雕作品,在波塞波利斯遗迹中属于保存较好的部分。因为材质的耐受力不同,那些采用亚述式样的砖瓦所构造的居室部分,已经完全坍塌覆灭。
\r\r波斯艺术家对于亚述文明的借鉴,我们能从波塞波利斯和苏萨两处遗迹的巨大建筑群中找到论据。比如,那些栩栩如生的薄浮雕和柱头雕刻作品。在波塞波利斯遗址所挖掘出的薛西斯柱殿中,有许多用作装饰的双翼牡牛和人头牡牛雕像。这些颇具现实主义风格的雕像正是效仿了亚述文明的特色,如面部为圆雕手法,身体则采用浮雕手法。在略有差异的细节处,则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艺术家们加以创新的地方。他们放大了圆雕手法中的表现形式,使其更加惹人注目。而在身体部分,他们取消了亚述文明中存在的五条腿的式样,削弱了原来那种故弄玄虚的风格。在刻画怪物的双翼时,他们采用了更为精致的处理手法,使其更加优美别致。在对人体的刻画方面,阿契美尼德的艺术家们没有直接临摹亚述作品的风格。我们曾在前文中提到,亚述艺术家们十分注重对人类肉体特质的刻画,同时在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强大力量的崇拜。这种精神追求表现在雕刻作品中,就会是夸张表现的人体肌肉和刻画细致的装束修饰。如果体现到极致,甚至会让雕刻作品成为一切事物的物质面貌的奴隶,变得很是刻板规矩。在后世人眼中,亚述文明中的雕像作品虽然生机勃勃、充满了力量感和运动感,但是未在此基础上做出突破。那种整体上的风格太过繁华秀丽,失去了在精神世界做出更多探索的空间。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波斯人则刚好相反,他们成功摆脱了物质世界对艺术创作的限制,将作品升华到了沉思冥想的纯粹境界。我们在研究迦勒底—亚述文明中的神灵时,不难看出他们身上的浓厚肉身气质。那种感觉充满了牺牲的味道,吸引了诸多如蝇子一般的信众。而波斯人在这方面更加纯粹,他们对宗教的感受停留在了对抽象观念和美好品质的感悟阶段,如神灵“阿美沙—斯朋陀”。萨尔教授认为,从迥然不同的艺术理念出发,波斯艺术一改亚述文明的华丽之风,变得超脱隽意且有肃穆之风。这是文明的进步,更是人类精神追求的进步。这种进步能够从两种文明的差别对比中看出,如两个时期艺术家们对衣着的细节的不同处理。我们在前文中提起亚述雕像,曾说到它们的服装大多是华丽厚重且仅仅依附在人身体上的。虽然被遮盖的身体线条不甚分明,但是在裸露的手臂部分,亚述艺术家们又用略微夸张的处理手法表现出肌肉的活动。相对而言,伊朗艺术家们对雕像衣着的处理则略显肥大宽松。但这种宽松,远不像西塞亚人的衣着一样空空荡荡,反而用审慎的手法达到了简洁高雅的效果和匀称适当的境界。这时我们能在作品中看到真正的端严庄丽,也能欣赏到柔和安适的线条美感。比如在薛西斯宫殿前的石阶两侧墙壁上,我们能看到浮雕里的塞种人、叙利亚人和其他纳贡者。笔者认为,这些作品与印度阿育王时代的艺术有密切关系,且二者的艺术造诣不分伯仲。常言道,物极必反,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伊朗艺术中体现出的脱离现实、有意简化的风格,有时会显得过于质朴,反而会有教条化和枯燥的感觉。这种缺陷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作品细节中,能充分体现出来。这种隽永飘逸的风格与罗马艺术或中国北魏的佛教艺术有许多相通之处。比如,他们的作品都具有神韵,还将前一期的异教造型技巧变得柔和起来,作品内容也变得空灵虚无。
\r\r \r\r□叙利亚及塞种人进贡者,薛西斯柱殿踏道,波塞波利斯
\r\r与大多数宗教相同,迦勒底—亚述雕刻作品中有形形色色的神明。当然,拜火教的信众们也造出了神像。在波塞波利斯遗址,我们发现了阿胡拉·玛兹达的造像。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君王的“弗莱瓦什”护神像。这个形象的来源可以追溯至萨尔恭王朝时期,我们在那时的军旗上就能看到长着双翼和轮的亚述神像。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艺术家们借用这一题材创作出新的形象,将“智慧之神”的形象刻画得更加超脱与唯美。这位神祇头戴形似软帽的低宝冠,穿着肥大袖子的衣服,还装饰有线条优美的日轮和涡纹。在神明身后,还有一双极大的羽翼作为背景存在,翅膀上面的条纹与衣服上的图案相互呼应。整体来看,这些细节都适合作为纯精神方面的宗教造像,与西方旧约圣经的风格类似,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主义。这个神祇造像代代沿袭,一直到了萨珊王朝时期,拜火教信众们才以他们的君王形象为模型,把它改为阿胡拉·玛兹达塑像。
\r\r在波塞波利斯和苏萨地区发掘出的浮雕作品中,我们能看到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诸位君王形象。这与萨尔恭王朝时的君王塑像有同样的风格,即类似的简约化。雕刻师们用心观察生活,在作品中表现一切细节。在那个时代,国王的形象较之以往减少了不少,只剩典型的四种。首先,是在圣火祭坛前参加礼拜仪式的端庄肃穆的君主;第二是制服敌人使他们臣服的君主,例如,在贝希斯敦(或比苏敦)地区所发现的石刻画卷中的大流士形象;第三是霸气威武登位临朝的君主,如在波塞波利斯城中一座中心建筑物的一面浮雕上的大流士形象;第四则是斩妖除魔、代表无上光明的君主。在这形形色色的图像中,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形象和阿胡拉·玛兹达的雕像有相似之处。例如,他们都戴着上宽下窄的软帽型的三重冠。这种特别的装饰物,被称为“希达里斯”。除此之外,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还穿着肥大的长袍。这种衣服与米代式样类似,又宽又长的袖子一直垂到脚面上,显示出尊贵的气质和庄严的感觉。君主常号令军队与民众,他的威严与气势可想而和。我们站在雕像作品面前,就能感受到那非凡不俗的王者气息。希腊人也十分爱戴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王,真诚地称其为“伟大的王”。更别提在那个时代,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整体领土面积十分庞大,堪称为前所未有。
\r\r前文中,我们曾提到过一块在波塞波利斯发掘出的薄浮雕作品。这幅作品的主题较为特殊,主要刻画了一个被民众所真心扶持的君主形象。那些被统治的民众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穿着各自的服饰服装,聚在一起拥戴这位仁爱睿智的君主。这幅遗迹的图形旁,还刻画着许多铭文,写道:“如果要弄清楚大流士陛下统治的领土有多大,那么看看这图中拥立他的不同民众就能清楚。并且我们还能知道,对于波斯帝国来说,它的利刃出鞘后,其锋芒毕露,直指最远的地方。”
\r\r \r\r□苏萨之彩釉炼瓦弓箭手
\r\r在苏萨地区,德·摩尔根氏带领考察团发掘出了彩釉炼瓦雕壁。这些遗迹能帮助我们完成在前面提到的课题,即对波塞波利斯所蕴藏文明作出的论述。仔细观察这些琉璃瓦,我们能发现它们的制造方法沿袭了亚述人的精神和思想。具体的例证从我们在尼姆罗德和科尔萨巴德两个地区发掘出的残片上可以看出,比如上面雕刻的国王、战士、雄狮、牡牛、鸟类和柳木等形象。到了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人承袭了亚述人的雕刻艺术,并极大地普及了这项技艺。他们还在此基础上进行组合与创新,比如将原来的小图像组成为装饰。相对比而言,波斯工匠们对色调和线条的处理更加细致,使最终效果更加美丽柔和,令人赏心悦目。同时,这些作品的意象崇高悠远,且因为对别致图形的重复而营造出一种堂皇富丽的感觉。现在收藏在卢浮宫中的,有一幅刻画着“射手”“雄狮”和“长着双翼的牡牛”形象的彩釉雕壁。我们细细观察,能看到射手们个个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他们穿着与君主类似的肥袖宽袍,头上戴着铁胄并用小带系着。为了攻击敌人,这些射手身上还装备着弓、箭袋和长枪。而雄狮的雕像同样运用了雄劲动人的手法,细致刻画出猛兽的肌肉与怒号的神情。与萨尔恭王朝的狮子塑像相比,这头狮像的写实风格略逊一筹,但是更有装饰性,富有审美价值。再看那幅长着双翼的牡牛,也是同样的风格,较之前朝文明少了雄健的风格,而多了华贵优美的感觉。
\r\r \r\r□苏萨之翼牛
\r\r简单来说,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艺术承袭了亚述文明的风格,并且变得更为恬静柔美。与萨尔恭王朝的艺术风格相比,此时期的作品没有刻意强调动态感和变化感,更加浑厚、肃穆,而且充满了庄严端丽的风格。在下一卷中,我们会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文明如何对孔雀王朝的艺术产生影响,然后了解它在萨珊王朝的艺术中是如何延续的。
\r\r 萨珊王朝的文明\r\r在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后,伊朗就一直处于希腊各王朝的统治之下。从公元前330年到前250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着。大约在这一时期,伊朗民族中的一个分支在科尔萨巴德地区独立了。此后,这支民族被称为帕尔提亚人,也称为安息人。古波斯语,称其为“帕尔塔瓦”,又叫“帕拉瓦”。这支民族所用的语言便被称为“帕拉维语”,是由古波斯语发展而来的一种伊朗方言。不管研究者们提出什么样的假说,都不能改变帕尔提亚人也就是安息人属于伊朗民族的事实。在那个时代,游牧在“外伊朗”地区的伊朗人,都被称为月氏人。有说法认为,帕尔提亚人中混杂有西塞亚人也就是月氏人的血统,具有雅利安人的特性。
\r\r公元前247—前224年,这一时期存在着一个由安息人所建立的阿萨栖兹王朝[4]。其创始人名为阿萨栖兹或阿沙克。自建立政权起,这个王朝便开始与希腊的塞琉西王朝争斗。我们都知道,国家间的争斗大多与领土纷争脱不了关系。阿萨栖兹王朝的士兵们在君主号令下,从希腊人手中夺走了伊朗西部、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领土。而希腊人不甘示弱,毅然对其宣战。而后,罗马人继承了希腊文化,并建立了强大的政权。阿萨栖兹王朝也没有放弃扩张领土,同样与他们展开了争斗。
\r\r阿萨栖兹王朝有两位著名的君主,他们都对王朝的政权稳固和疆域拓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一位是密斯利德提斯一世,或被称为密斯拉德特大帝。他于公元前174年至前136年在位,主要功绩是奠定了安息帝国历史上由玛尔夫到巴比伦尼亚的疆域。另一位是奥罗德斯,他继承了先王领土,主要功绩是抵御外敌入侵。公元前53年,罗马帝国由克拉苏执政,发起了对阿萨栖兹王朝的攻击。奥罗德斯积极应对,在卡里地区成功阻拦了敌人。我们顺着时间线的发展,纵观阿萨栖兹王朝的历史路径。它恢复了伊朗的独立,并且在长达四个世纪的时间里,都能保证政权的稳固和领土的完整。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它都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继承者,并且担得起“大王”和“列王之王”的称号。尽管有许多英明的君主在治理国家,但伊朗文明总是显得十分低调。与影响力强劲的希腊文明相比,伊朗文明似乎还处在蛰伏的状态中,毕竟亚历山大大帝的铁蹄所及之处,都或多或少带着希腊文明的色彩。
\r\r从建立政权开始,阿萨栖兹王朝就与希腊人争斗不休。伊朗的版图一度曾由叙利亚伸展到印度河流域,并且因为领土问题与希腊、罗马的君王们刀锋相向。但是战场上的对阵,没有影响文化间的交流沟通。阿萨栖兹王朝的人们从上到下,对待希腊文化都秉持着友好的态度。比如在货币流通方面,他们所铸造的钱币都有“亲希腊人”的称号。在铸造技艺和设计灵感等细节上,这些钱币借鉴了希腊人的文化特色。钱币上雕刻的铭文也是用希腊字组成的,学习希腊文化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不管是阿萨栖兹王朝的诸位君王,还是同一时期统治着大夏和印度河流域的贵霜王朝的诸位君王,他们都不约而同采纳了希腊人的习俗,或多或少开始变得“希腊化”。这固然与个人兴趣爱好有关,但更多的因素在于时代趋势。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据说在两国交战,罗马君主克拉苏的人头被斩下呈上来时,阿萨栖兹王朝的奥罗德斯王还在入迷地听欧里庇德斯所写的戏剧。在希腊文化发挥极大影响力的同时,雅利安精神仍有其存在的据点——波斯。毕竟,拜火教的精神是最不会妥协的。希腊人将波斯本部称为波西斯,也就是现在的法尔斯省。这个地区的历史韵味厚重,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世袭统治之地。在法尔斯省内,统治当地的诸侯一般都是塞琉西王朝的藩属。后来,此地的人们又臣服于阿萨栖兹王朝。在现代发掘出的他们铸造的钱币上,我们能看出这群人对拜火教的虔诚信奉。但这种信仰并非永久持续的,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在公元后第三世纪初叶,法尔斯省内的民众又转向了萨珊王室。巧妙的是,萨珊王室同样发源于拜火教祭祀家庭。公元前224年,萨珊王朝的君主阿打失一世举起义旗,浴血奋战推翻了阿萨栖兹王朝的政权,并杀死了这个王朝的最后一位帝王。胜利的果实总是充满芬芳,为人们带来诸多欢愉。譬如阿打失一世胜利后,便自立为全伊朗的王中之王。当然,他所统治的版图并不包括那时的大夏,那里仍然由大月氏人拥戴的贵霜王朝占据。萨珊王朝的首都有两座城池,一个是在法尔斯省内的伊斯塔克尔地区,位于故城波塞波利斯的北面;另一个是在迦勒底的泰西封—塞琉西双城,即维·阿打失,这里原来是阿萨栖兹王朝的首都。
\r\r公元224—652年,波斯始终被阿打失建立的萨珊王朝所统治。这个政权自成立起,便始终以保卫伊朗及伊朗文化为一贯宗旨。它不仅对抗着西方的罗马人和拜占庭政权,还抵御着东方代替外乌浒河的贵霜王朝而崛起的突厥人。突厥人是蒙古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5世纪时是嚈哒白匈奴人,到了第6世纪后半叶时成为突厥人。
\r\r萨珊王朝诸位君王的心愿,是复兴曾扬名天下的阿契美尼德帝国。他们越过伊朗本部边境,试图将领土的范围扩张到从兴都库仕山直达地中海。萨珊王朝的第二代君主沙普尔一世(公元241—272年在位),始终未曾停下征伐的脚步。公元259年,他俘虏了罗马帝国的君主瓦利里安。这是一次惊人的胜利,理所应当被铭刻到萨珊王朝的石刻上作为纪念。随后,沙普尔一世又继续征伐叙利亚,但是没能持续占领当地。公元531—579年,统治萨珊王朝的喀斯鲁大帝,他是王朝末期较为杰出的君主。人们又称其为克斯劳埃丝(或称喀斯鲁)一世阿努希完,寓意着“灵魂不朽的人”。这位帝王长于征战,不仅成功侵入叙利亚,还在公元540年奇袭攻取了安提阿城。他的脚步没有就此停下,反而继续开拓疆土,一直远达也门地区。在喀斯鲁大帝之后,他的子孙们也继承了同样的野心。公元590—628年,治理萨珊王朝的是克斯劳埃丝二世帕维兹。公元613年,这位君王收服并统治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小亚细亚,并且一度夺得了君士坦丁堡。公元628年,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赫拉克琉斯发起反击,在美索不达米亚本土打败了帕维兹。
\r\r除了向西方扩张版图之外,萨珊王朝的诸位君主也在东方展开了行动。他们用饱满的热情和诚恳的努力,不断保卫并扩张雅利安主义。公元276—293年期间,巴拉姆二世瓦拉兰在位。他最为人所称道的功绩,是从萨迦王朝末代君主手中夺取了塞伊斯坦地区。公元303—310年,荷尔米兹二世在位。他当政时,开始拥有支配在喀布尔地区的贵霜王朝国君的权力,还娶了那位国君的女儿作为妃子。4世纪末期,蒙古人种的一股势力崛起,主要由游牧民族嚈哒人组成。他们迅速从贵霜王朝的末代国君手中夺取了外乌浒河地区,又在公元425年占领了大夏和喀布尔,其实力不容小觑。出于扩充疆土的雄心壮志,这个游牧民族继续开始攻打萨珊王朝。双方展开了厮杀,过程十分艰辛。公元420—438年,萨珊王朝由巴拉姆五世统治。他名叫巴拉姆·古尔,击退了崛起的游牧民族势力。但其后的继任者腓鲁兹(公元459—484年)没能维持这种胜利,反而于公元484年在巴尔克地区被敌人所杀。正面杀敌不能取胜时,人们往往会选择盟友来壮大势力。而后的公元565年时,萨珊王朝的喀斯鲁一世联合中亚的另一民族——突厥人,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土耳其人,一起对抗劲敌嚈哒人。最终,这场战争以嚈哒人走向覆灭为结局,其统治下的领土尽为萨珊人和突厥人所瓜分。具体来说,萨珊王朝收复了大夏,而突厥人则取得了索格地安即乌浒河地区的统治权。这个时期,波斯帝国最为瞩目的成就,就是将其版图扩展到大夏。最能证明这一点的证据,是两个分属不同政权的地区出现了同类的壁画。前者是安德烈·戈达尔夫妇在巴米延即梵衍纳所见到的萨珊—佛教壁画,后者则是哈金氏在杜克塔尔—夷·奴希尔番所见到的壁画。然而领土有扩张就有缩减,这都是历史更迭的常态。经过数年,突厥人在外乌浒河的政权稳固之后,他们开始打起了萨珊王朝的主意,将大夏从旧日盟友手中夺走了。
\r\r在萨珊王朝立国的初期,其国君就开始恢复原来的民族、宗教和治理体制。在这个政权存续期间,这个王朝上上下下的民众都信奉民族主义,也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从铭文和钱币中,能看出萨珊王朝真实的民族特质。这个王朝对于国王尊号的设计,也有很微妙的变化。从希腊式的“王中之王”和“希腊人之友”,变化为“奥尔玛兹德之仆”和“阿利亚之王”。其中“奥尔玛兹德”是一种帕拉维语,代表阿胡拉·玛兹达。萨珊王朝的诸位国君十分看重其王位的政治意义,他们直接越过了马其顿或帕尔提亚的篡位者,自称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继承人。他们还特意将本国帝王阿打失一世,与大流士、薛西斯的血统与姓氏联系起来,编制出一个宗谱。但从文明的传承角度来说,阿契美尼德王朝与萨珊王朝可谓泾渭分明。具体来说,前者大量汲取了亚述—巴比伦文明和希腊文明的精华,而后者,即阿打失与他的后裔们,始终完全属于波斯。大流士帝国发展至末代时期,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它同时被希腊人和萨迦人守护与保卫。但萨珊帝国并没有这样的特质,它始终属于伊朗民族,并且严格意义上属于其中的分支——雅利安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腊—罗马帝国,它的政权更迭频繁,导致了各民族都曾有握得权柄的时候。我们细致列举这个帝国中的历代皇帝,就能看到其中有西班牙人、叙利亚人、非洲人和伊利里亚人。萨珊帝国则没有如此多元,帕尔提亚政权的统治者们是清一色的伊朗人。在这个帝国最为多元与包容的时期,也只是当权者允许在某种可控的范围内,使亚美尼亚和叙利亚的文化与本民族的帕拉维文化并存。
\r\r萨珊王朝以民族的情感为基础,重兴了由大流士所建立的高效的行政机构。帕尔提亚政权即安息政权充斥着封建主义,帕尔提亚政权有着和君王几乎同等的权力。从根本上来说,它与那些世袭的“萨拉特普”完全相悖,所以不断产生纠纷。在党派之间的权力倾轧之下,萨珊王朝的君王们并不能完全消灭这些封建贵族,也未能解除他们世代承袭的职位。但是其斗争的结果是成功的,因为诸位君王获得了世袭贵族的拥戴。而后,中央继续收服地方势力。从边疆长官“玛尔兹班”和“拉德”,到省区长官们与大地主庄头们(“沙里干”和“狄克汗”),都尊服至高无上的帝国统治者。
\r\r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伊朗复国与琐罗亚斯德的拜火教有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萨珊王朝的初代国君曾经命人编订了一部完整的玛兹达教圣书——《阿吠斯陀》。这一部圣书一直流传到今天,是研究史实的重要资料。在宗教政策方面,萨珊王朝颁布的敕令也与阿契美尼德王朝有所不同。虽然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时期,民众们也信奉阿胡拉·玛兹达,这种崇拜与信仰实际上是一种一神教。严格来说,他们并不像是琐罗亚斯德的教徒。冈比斯王去世时,玛兹达教人篡夺了政权。自此之后,这个王朝再也不信任祭司阶级。但是在另一方面,萨珊王朝的诸位君王却对教士们给予了极大的信任,任由他们占据政府高层的职位。随着这个王朝的正式建立,一个正式的教会也产生了,即由类似教皇的“摩巴丹—摩巴德”领导的一个拜火教徒的组织。任何事情超出合理的度之外,就会将局势的平衡打破。在贵族的支持下,教会势力变得愈发强大。这种形势发展到4世纪时,君王统治的政府力量也开始警觉,想办法抵制教会的侵蚀。但是诸位君主在实施对抗教会的策略时,却得到了惨烈的结果。阿打失二世(公元379—383年)被废黜,沙普尔三世(公元383—388年)和雅兹达伽德一世(公元399—420年)都被杀害,巴拉什(公元484—488年)被大贵族和拜火教徒们弄瞎了双眼。最后一位要实施改革的君王,是卡瓦德或称阔巴德一世(公元488—531年)。为了限制贵族们和拜火教徒们所享有的社会特权,他不惜同意了玛兹达克的财产公有的主张。但是最终,卡瓦德也遭到了放逐。后来,他又成功复位返回国家,恢复了正式的宗教传统。诸位君王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证明了政治宗教原则是不可撼动的。萨珊朝君主专制政体与玛兹达正统教会的联盟,是十分稳固密切的。
\r\r 萨珊王朝的艺术\r\r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散落着不同艺术风格的璀璨明珠。通常而言,迥然不同的两种艺术风格就如两颗光滑的珠子,无法衔接在一起。但由于萨珊王朝艺术的存在,古老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艺术和穆罕默德教的艺术能够前后贯通。实际上,这种联通作用使萨珊王朝的艺术显得格外重要。
\r\r在建筑物设计方面,卷屋顶的形象很引人注目,曾出现于帕尔提亚时代的哈特拉地区。那时的人们很推崇罗马文化,便学习了这一特色。一直到了萨珊王朝,工匠们引用卷屋顶成为普遍现象。萨珊朝的第一座王宫是阿打失一世(公元224—242年)的王宫,它坐落在法尔斯省的非鲁扎巴德地区。在后人勘察时发现,这座宫殿的一间门厅就采用了卷屋顶风格。这一点,从它有一个呈筒形的穹隆就能看出来。而后,在法尔斯省的另一座宫殿中也发现了类似风格的使用。在那座名为萨尔维斯坦宫的建筑顶部,工匠们精心搭建了卵形的圆屋顶。经过对这种拱形厅堂的研究,萨尔教授与赫兹菲尔德教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们都认为,这种设计风格带有伊斯兰教礼拜寺的色彩。细细总结,这正是埃完建筑的原则。
\r\r在萨珊时代,颇为后人们所称道的主要遗迹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坐落在泰息封地区,由沙普尔一世(公元242—272年)命人修建的“喀斯鲁圆顶殿”。这座建筑又名为“塔夸—夷·基斯拉”,颇为恢宏壮观。它的中间部分是觐见室,被设计成广大的圆顶宫殿。历经沧桑之后,宫殿内部的椭圆形穹隆已经逐渐坍塌,只剩下巨大的拱形结构。站在这遗迹面前,不能不想到多年后波斯的清真寺,那优美的圆顶与眼前的拱形结构是何其相似!
在宫殿的两侧,还有未被风雨击倒的残留墙壁,上面有叙利亚风格的建筑构件,比如一行一行分布的圆拱、壁龛,和分为上下四层的建筑形式。
坐落在波斯库地斯坦的遗迹,即“夸斯尔—夷·希琳”宫殿,对于后人的研究也颇为重要。它是喀斯鲁二世(公元590—628年)命人修建的,并且特意以他的宠姬命名,建在一个三百英亩的园林中。这座宫殿占地面积较广,主要由两处主殿组成。其中一处是外观为正方形、顶部有椭圆顶阁的勤政殿,整体瑰丽宏伟,名为“夸拉阿—夷·恰哈尔·夸庇”。另一处宫殿名为“伊玛拉特—夷·喀斯鲁”,有类似的风格,同样是方形外观,有圆形顶阁,主要功用是作为觐见室。但与众不同的是,这一处宫殿并非从平地建起,而是建造在一个平台上,下面由圆拱支撑。想要到达这处宫殿,必须从旁边的斜坡通道往上,并穿过24根柱子的走廊。这一群建筑物的设计特色鲜明,让人想到波塞波利斯的大流士宫殿,和那里的薛西斯的宫殿。在它整体的布局上,比如花园和凉亭的分布规格,让人联想到伊斯法罕地区的宫殿,特别是萨法维王朝的王宫。
\r\r根据研究我们知道,萨珊王朝艺术与伊斯兰教时代的波斯艺术有诸多相似之处。如果萨珊王朝的艺术品遗迹中的装饰能够一直保存到现在,就能证明这句话所言不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塔夸—夷·基斯拉宫,这座宫殿中一定布满了绘制在灰泥上的装饰图画。但可惜的是,它们都没能躲过战乱的损毁,没有保存下来。这座宫殿的主要结构部分所用的墙壁和柱子,似乎质量都很差。所谓的墙壁是在石块和石子外层涂灰泥而成,柱子则是用平整的砖搭建而成。和后来波斯建筑师们相同的是,萨珊王朝的建筑师们也用没那么坚固的材料制成建筑物。因为每一代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喜新厌旧,热衷于放弃前朝的宫殿而后造出一座新的。为了达到君王们满意的效果,建筑师必须将宫室表面的装修设计得十分精妙。他们在墙头的琉璃瓦上用灰漆绘制的彩色装饰,代表着每个王朝的荣华气息,但是这些装饰会在时间的腐蚀下变得斑驳破碎。这种不可逆转的剥落损毁,正是萨珊王朝大部分绘画和雕刻缺失的原因。对于世界艺术研究者来说,这是十分可惜的一件事。当然,工作人员也在其他地方发掘出了不少遗迹。比如夸什—夷·鲁斯他姆或塔夸—夷·布斯坦地区的岩石雕刻,或者是在杜克塔尔—夷·奴希尔番地区那些人迹罕至的岩洞中的壁画。这些遗迹都因为其本身的特性或所在位置的优势,得以完整保存下来。仔细观察之后,我们能看出这些作品代表着一个极有力量的艺术派别。
\r\r公元242—272年,沙普尔一世统治着萨珊王朝。在他当政的时代,出现了许多精美绝伦的岩石浮雕作品。比如,在法尔斯省内波塞波利斯附近的那夸什—夷·鲁斯他姆地区,就保存着许多有代表性的艺术品。在卡兹伦以北的方向,沙普尔一世还命令工匠们以自己的名义创作了浮雕作品。最常见的主题,就是大神奥尔玛兹德授予君王权杖的场景。在那夸什—夷·鲁斯他姆地区发掘出的雕像遗迹,上面刻画的国王正是萨珊王朝的开国之君阿打失。在这幅作品中,国王与神祇相对而坐在马背上,一个授予冠冕一个接受冠冕。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两匹马的形状全然相同。而且神祇与君王的形象除了在特有标识与头饰上有所不同外,其余部分可以说是完全一样。这样严格对称的设计仿佛是有意将君主刻画为神祇的复本,体现出虔诚又坚定的“君权神授”的观念。上帝与君王相互接近时的姿势并不仅仅是手指的一次触碰,而是一次封建专制性质的授权。在罗马塞斯丁教堂藻井的壁画上,曾出现过神祇与人的手指触碰的设计。它所刻画的场景是耶和华与亚当的一次触碰,他们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代表着神人之别的深渊。显然,在君权神授的封建体制下,人类中的统治者会认为自己与天上的神祇一脉相传。这种联想充满了雄壮与庄严的感觉,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而最能表现这种风貌的作品,当属君王与他们所信奉的神祇相互平等面对的形象。这种设计无疑受到了玛兹德教精神特质的影响,或多或少承袭了它的思想观念。
\r\r在萨珊王朝的艺术发展方面,能够让我们想到亚述—阿契美尼德文明的作品数不胜数,这要先从那有着层层鬓鬟的皇室典型人物算起。纵览那形形色色的艺术品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萨珊王朝的浮雕作品都有一个很普遍的特点:在细节方面,它们消除了过于烦琐的细部;在造型方面,它们则比波塞波利斯的遗迹显得更加雄健有力。这种整体上的感觉,与阿契美尼德王朝作品给人的印象颇为相似,甚至我们有时会觉得萨珊王朝的作品更加有力而沉重。艺术品在精神气质方面的变化,代表着那个时代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这种沉重的风格,就宣告着中世纪的来临。例如,我们可以把那夸什—夷·鲁斯他姆地区发掘出的浮雕作品中的马匹,与波塞波利斯作品中的马匹相比较。仔细端详之后,我们很快发现二者有明显的不同。那些代替居鲁士和大流士的轻骑兵的人,是披挂铠甲的骑士,他们的坐骑都是可以拖车负重前行的健壮马匹。
\r\r在学术界,萨尔和赫兹菲尔德两位教授对萨珊文明的研究颇有建树。他们指出,在波塞波利斯附近的那夸什—夷·拉甲布地区,发掘出了一幅类似的授权图。这幅遗迹已经残破不堪,但我们仍能从中发现,它比前面提到的那幅作品有所进步。这种进步十分明显,主要体现在刻画技巧上。在对于君主形象的刻画方面,取代过去那厚重皇袍的,是宽松有褶皱纹路设计的长袍。这样一来,人物就显得更加高雅和生动。刻画同样题材的作品,还有沙普尔地区的岩石壁画。画上的人物是巴拉姆王一世(公元273—277年),他正在从奥尔玛兹德神手中接受皇冕。这里的马匹并没有过分挨近,却表现得十分真实,富有生气。我们很快就联想到了,它与意大利雕刻家佛罗基俄氏的作品有类似之处。此外,雕刻师们表现的场景并不是神祇与君王同时拿着冠冕,而是神祇将王冠送与君王,而君王则十分自然地伸手去接。最后,正像萨尔教授所说那样,这幅作品中那带着褶皱的长袍更好地表现出了这两个崇高的形体。整体而言,其效果会比那夸什—夷·拉甲布地区的那幅作品更为开朗而且精美。
\r\r公元259年,沙普尔王生擒了罗马皇帝瓦利里安。这件事不仅在政治上有深刻的意义,在艺术方面也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整个萨珊王朝的雕刻家们,都会因为这个题材而迸发出更多的创作灵感。在那夸什—夷·鲁斯他姆地区发掘出的雕像作品中,沙普尔王坐在马背上,他的姿势与受冠图中的其他君王十分相像。而屈膝跪在他面前的人,正是战败被俘的“恺撒”。在沙普尔地区发掘出的诸多浮雕,都将这一题材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甚至意犹未尽的雕刻师们,还由此刻画出成为著名场面的第二阶段。具体来说,就是这位“万王之王”沙普尔正携着自由民希里阿底斯的手,把他送到罗马军中去做领袖。在后面跟着的是骑兵随从们,而瓦利里安则跪在地上一言不发。这幅作品的整体风格充满了活力,且有磅礴恢宏的气势。与此风格类似的作品,是沙普尔地区发掘出的另一幅以巴拉姆王二世为主题的浮雕。与列位先王一样,巴拉姆王二世同样骁勇善战,他曾打败了一个属于阿拉伯人种的外族。这幅作品便是以此为题材,用熟练的技巧刻画出马匹、骆驼和蛮族的服饰型式。其精致程度,可以与波塞波利斯的塞种人和叙利亚进贡图相媲美。
\r\r \r\r□(左)银盘,前萨珊朝时代
\r\r \r\r□(右)雕有喀斯鲁二世行猎图的银盘
\r\r萨珊王朝的艺术作品种类多样,并不局限于庄严凝重的“授冕”题材。诸多浮雕作品中最为令人瞩目的,乃是气势生动的风格。在那夸什—夷·鲁斯他姆地区,也发掘出许多刻画战斗场面的作品。比如,在一些马上战斗的场景中,雕刻师巧妙地将其中蕴含的运动感表现出来,其中一个细节就是君王或骑士用长矛刺死了一名罗马士兵。君王纵马前奔,用自己的力量折断了罗马人的兵器,还将对方军队冲击得人仰马翻。这种场景充满了惊险刺激,与中世纪骑马比武的场面十分相像。这幅作品的构图恢宏雄壮,还有着十分活泼饱满的意境。如此这般的精神风貌,可以与萨尔恭王朝的纪念石刻作品相媲美。
\r\r在基尔曼沙东北方向的塔夸—夷·布斯坦地区的石窟中,同样发掘出了类似风格的作品。其中有一幅石雕是要献给喀斯鲁二世的,其内容正是以这位君王为主题的骑马像。整体风格十分优雅美丽,而且它的雕刻高度也令人瞩目,几乎和圆雕一样了。这块石雕的左侧,描绘了君王在沼泽地猎取野猪的图景。我们大致能看到这样的场景:骑着大象的猎人们将野猪从芦苇丛中驱赶出来,君王则站在一艘小船上引弓搭箭,试图瞄准猎物。在他们后面跟着一些小船,里面坐满了为行猎伴奏的乐师。有两处值得注意的小细节:一是猎人们所骑着的大象,和印度阿丹陀及摩婆里普拉姆的雕刻艺术中的大象形象类似;二是这种为国王狩猎伴奏的题材流传较为久远,一直到萨法维朝时代还能见到。同时,雕刻师们在处理受惊乱跑的野猪形象时,会用强烈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比如,他们会刻画在乱箭中受伤的野猪,跌落在君王所乘小舟的附近。在这块岩石浮雕的右侧,描绘了一幅君王和侍臣们追逐野鹿的图景。一群野鹿本来藏在隐蔽处,被人类的声音所惊吓开始四处逃跑。逃遁、奔跑的兽群和跌倒的动物,都在雕刻师笔下变得活灵活现。那行动细节处的逼真,与阿述巴尼—帕尔地区发掘出的猎野山羊的浮雕作品不分伯仲。当我们看到波斯细密画中所描绘的鹿类动物时,不要忘记刚刚提到的猎鹿图,也要记得在杜克塔尔—夷·奴希尔番地区发掘的壁画作品。事实上,波斯人在艺术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丢掉他们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在对动物的刻画与表现方面,这种传统还与印度的孔雀王朝、笈多王朝和伊斯兰教时代的艺术有关。
\r\r雕刻在岩石上的作品虽然看起来坚固,实际上却有着它脆弱的地方。比如,雕刻师们因为材料的坚硬而很难完全掌控作品的水平,或者这些作品都会或多或少因为时间的变迁而有所损坏。虽然有这些挑战存在,但是萨珊王朝艺术中的金属盘片却保存得完好无缺。它们多以动物生活或者英雄事迹为主题,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其中堪称为代表作品的,是两面精致的银盘。其中一面现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中,是优康宁罕氏所发掘的遗迹,是一幅巴拉姆·古尔王的猎狮图;另一面则被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中,是一幅喀斯鲁王二世的行猎图。这两幅作品都有各自的杰出之处,堪称为伊朗的伟大作品。在巴拉姆·古尔王的猎狮图中,主要表现了这位君王与一窝狮子搏斗的场景。他的左手抓着一头挣扎的小狮,又用右手执剑砍中了迎面扑来的雄狮头颅。较为凶险的是,还有一头雌狮正向这个“破坏者”冲过来,咬到了巴拉姆·古尔王的战马胸部。萨珊王朝的战马虽然雄健,但是还会因为疼痛而扬起前蹄。这整个一组画面充满了悲壮的气氛,可以与萨尔恭王朝最富于戏剧性的狩猎场面相提并论。我们也能在这些画面里看出亚述文明的痕迹,比如那头暴怒着窜冲过来的狮子形象,是一种很典型的亚述艺术的形式。在喀斯鲁王二世的行猎图中,同样充满了华丽优美的特点。这个古代的亚述君王乘着马车肆意驰骋,他正向一群野猪、鹿和野山羊射出如雨一般密集的利箭。在细节处,我们能看到因为飞速前进而飞舞的披风上的飘带。而“科丝蒂”和马具上的流苏,则在逆风状态下更加显眼。还有那些因为中箭滚倒或四处逃窜的动物,都运用了逼真而精确的技法来刻画。这种技法可以达到让人们“分辨出不同动物”的程度,是库雍吉克和科尔萨巴德的大师们从古代的东方文明中学到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动物雕刻家们一直存在着,一直到伊斯兰教统治时期。可以佐证这一观点的史料很多,比如我们能在伊斯兰教最鼎盛的时期,发现许多晚出的纯萨珊王朝式技艺的作品。例如,索尔提科夫氏收集到的一个刻有精美猫科动物的银碟,现被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中。能够与之相比的,是杜西特氏收藏的黑石圆雕的一个怒吼的雄狮头像。根据维各涅尔氏的推断,这狮子头像的年代约在公元4世纪到5世纪之间。当我们研究到拉伊的伊斯兰教陶器时,我们应当察觉到类似的情形,不应该忽略维各涅尔氏收藏的萨珊王朝陶器。那些陶器大多装饰着拜火教人物的形象,或者动物图像,如骆驼及山羊。
\r\r法国考古团在阿富汗有了新发现,他们为史学研究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因为近年来,研究人员一直认为萨珊王朝的绘画作品未曾流传下来。戈达尔夫妇用特殊技术复制的岩石壁画,成功填补了这一块空白。这些作品确切来说属于公元3—6世纪的巴米延,主要题材采用了萨珊王朝的式样,同时还具有印度文明与希腊文明的艺术特质。虽然这些壁画带有佛教的色彩,但是画中的人物却具有萨珊王朝君王的特色。我们仔细观察就能看到,画中人那整洁的长发,软冠式样的、装饰着新月和日轮的冠冕,还有飘扬在两面肩膀上的“科丝蒂”。这飘扬的装饰物有着似曾相识的式样,它与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所藏银盘上的巴拉姆·古尔王和喀斯鲁二世所佩戴的饰物有类似之处。这种微妙的类似,其原因在于萨珊王朝和白匈奴人之间,为了巴尔克和巴米延两地曾经有过长时期的斗争。最后,巴米延被并入了喀斯鲁一世帝国的版图。研究人员在巴米延地区还有新的发现,那就是在当地的壁画中还有许多新出现的人物。这些人物站在印度僧侣、犍陀罗派的佛陀身旁,在纯罗马风格的四匹马所拉战车旁边。他们穿着宽边长袍,在腰间系着一条窄带子,并且拿着长剑和矛。在各方面的细节中,这群人物都与中国新疆地区的克孜尔壁画上的骑马人相似,都具有同样的伊朗风格。克孜尔壁画属于7世纪,是由德国格伦威德尔和冯·勒考克两位教授领导的考察团发掘的。在巴米延地区的这幅壁画上,有着沙普尔、巴拉姆和喀斯鲁的王者形象,他们都与克孜尔骑马人相类似。二者可以并列在一起,证明伊朗风格的绘画广泛存在。无论是佛教还是摩尼教,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萨珊王朝艺术风格的影响。公元7—9世纪的中亚,自库车至吐鲁番盛行着摩尼教。这个教派的绘画作品有很浓烈的伊朗风格,可以说是伊朗绘画的一个地方性分支。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研讨中亚文明的艺术风格。确定过这一点后,就能更好地认识斯坦因爵士在喀什噶尔的丹丹乌里克地区发现的壁画作品。这幅画作属于公元8世纪,主题是佛教中的神“金刚力士”形象。巧合的是,这个形象与萨珊王朝的君王有诸多类似之处。那黑色的胡须,头上戴着王冠,身着绿袍与高靴,极像某一代巴拉姆王或者喀斯鲁王的形象。在这铁一样不容置疑的事实面前,我们必须承认在那几个世纪中,萨珊王朝的艺术风格有着极其广泛的传播范围。从大夏和外乌浒河等地区到大戈壁的沙漠腹地,都能找到这种影响的痕迹。后来伊斯兰教在伊朗本土灭亡萨珊王朝的政权时,这种影响仍然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
\r\r在巴米延的壁画中,我们还能看出萨珊王朝的作品有充分的原创性和艺术性。与此同时,这些画作中也或多或少显示出了西方古典艺术的渗透痕迹。在西部的那夸什—夷·鲁斯他姆的岩石浮雕上,在雕刻有最初几代国王造像的钱币上,我们都能从细节处看到罗马文化的影响痕迹。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持续,反而很快就被同化了。在类似的情况下,东部的大夏地区,如巴米延的壁画中,能观察到萨珊王朝的艺术作品曾与犍陀罗的希腊式佛教艺术相遇,二者碰撞出了微妙的火花。但这种影响对拜火教的杰出作者们来说,是有些生疏的。更加有趣的是,萨珊王朝的艺术同样在东部遇到了印度笈多王朝的文明。在长时间的接触中,雕刻师们所运用的技法也变得类似起来。塔夸—夷·布斯坦、阿旃陀和摩婆里普拉姆的动物雕刻家们,在各自的作品中都展现出相似之处。这种类似之处表现得最明显的,当属阿富汗卢伊附近杜克塔尔—夷·奴希尔番地区的岩石壁画。1924—1925年,学者哈金氏发掘出这些宝贵的遗迹。1927年,巴尔托克斯氏又重新考察了它们。与巴米延的壁画相比,这些岩石壁画更加具有伊朗风格。根据哈金氏所说,在公元570年左右,喀斯鲁王一世征服大夏之后命人绘制了这些壁画。最为奇特之处在于,画上中央的人像所戴着的头饰上有一颗狮子头。根据赫兹菲尔德教授推断,画中表现的人物形象是大夏总督,也是萨珊王朝的亲王。在杜克塔尔—夷·奴希尔番的壁画上,还出现了一个人物。在哈金氏看来,这个形象与那夸什—夷·鲁斯他姆第Ⅵ号浅浮雕上的沙普尔像类似。哈金氏还指出,这种联系不仅存在于王者造像上,还存在于动物图像和妇女绘像中。壁画中的羚羊、野羊、牛、鹿、狮子和大象等,为笈多王朝的艺术和塔夸—夷·布斯坦的动物画家们建立了一种联系。而且这些妇女造像与印度笈多派和阿旃陀绘画的作品有着更加直接的血缘关系。说到此处,我们可以回忆两派绘画艺术自开始起就有的亲缘。在波斯阿契美尼德文明与印度孔雀王朝丧奇地区的雕刻作品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现在我们能发现,印度笈多王朝及其后面的绘画作品,与同时代即公元6至7世纪萨珊王朝的作品之间,也有同样的亲缘关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印度和伊朗的文明之间,保持着艺术方面的互相影响。并且这两派绘画艺术之间有着相同的题材,尤其是在动物图像及其表现手法方面。综合而言,这是十分正确的结论。
\r\r这个时代的波斯艺术,有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方面是自然主义的面孔,它造成了萨珊王朝艺术和印度笈多王朝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纹章式的艺术,具有装饰性的程式化倾向。就像我们所观察到的一样,这种趋势继承了迦勒底—亚述文明中的装饰艺术。由于拜火教对抽象事物和严格教条的爱好,更加强了艺术家们对这种艺术风格的偏好。所以,到萨珊王朝时期,伊朗艺术的形式已然定型。基于这样的基础,伊朗文明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风格,并且还在很大范围内持续传播。从高加索民族、俄罗斯草原的游牧民族,到北方的蛮族、哥特人、斯堪的那维亚人,本地的日耳曼人,和在东北方的匈奴与突厥的游牧部落。特别是在他们的织造品和金银工艺品中,能够看出萨珊王朝的装饰艺术家们是如何产生影响的。
\r\r这些艺术家们能够在不同的生活题材中剥下其造型特质,并且巧妙地把这个特质从活的形态中提取出来,成为纯几何形的图案。在欧洲的博物馆和教堂的圣器安置所中,都收藏着许多萨珊王朝的织造品,以及一些风格类似的作品。在这些织造品上面,就有程式化的幻想怪物。这种风格的体现,都是为了取得良好的装饰效果。有的怪物是头和前爪像猫,而双翼和尾部像是开屏的孔雀,被称为“龙孔雀”;有的图像是骑士坐在半狮半秃鹫的“格里芬”或长着双翼的狮子身上,与其他的“格里芬”作战;有的图像则是完全对称的一对野羊或者雄狮,它们扬起前足相对而立,组成了一幅精美的图案。除此之外,有的怪物题材是迦勒底—亚述艺术家们所喜欢的程式化的狸形野兽吞吃鹿类的图案。这种花纹在蒙古诺音—乌拉地区的匈奴人织造物中也出现过,是由科兹洛夫考察团发现的。
\r\r虽然不同的文明和艺术之间会互相影响,但是萨珊王朝的文明并没有影响到安息—萨尔马提亚地区的艺术。公元前3世纪时,萨珊王朝刚刚出现。而在几个世纪之前,安息人已经消失了,并且萨尔马提亚人也即将被哥特人和匈奴人所消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萨珊王朝纺织品对3世纪至10世纪间中亚的织造品是有深远影响的。比如上述我们提到的那些程式化的鸟类、“格里芬”和怪物互相斗争的花纹,都被法尔克博士的研究证实对中亚织造品有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这些萨珊王朝所特有的装饰图案,不仅能在埃及和波斯的伊斯兰教时代的织造品中看到,而且在伊斯兰教初期时代的作品中也出现过。法提马王朝,即绿衣大食统治时期,在高加索至埃及地区所遗留下的青铜器皿,尤其是在鸟形或者麋鹿形的水罐上,我们都能看到萨珊王朝特有的动物图案。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萨珊王朝风格錾花和“敲花”的铜质水罐。这一文物曾经是勃布林斯基氏的收藏品之一,现被存放在埃尔米塔什博物馆中。我们仔细观察,能看到那些浑厚凝重的狮子、马匹和鸟的形状图案。它们是如此的精美优雅,被当作许多器物装饰的原型和范本。比如法提马时代阿拉伯的“阿夸玛尼里”,即饭后所用的盛放蔷薇水的碗,和中世纪西欧的铜质日用品,都借鉴了上述图案。
\r\r综上所述,我们想要对伊斯兰教的艺术有所了解,必须明白的是萨珊王朝艺术所具有的双重倾向。其一是用自然主义手法表现活的物体,特别是动物;其二则是他们的装饰性图样和抽象的几何图案,在亚洲文明发展中起到非常突出的作用。
\r\r[1]阿契美尼德王朝:被称为波斯第一帝国(公元前550—前330年),创建者为阿契美尼斯,阿契美尼斯死后,由他的儿子泰斯帕斯继位,并带领阿契美尼德脱离了米底王国的统治。居鲁士二世继承冈比西斯一世的王位后,击败了当时统治波斯的米底人,统一了波斯,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继位的大流士一世陆续入侵和征服了世界上五大文明发祥地中的四个(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埃及和希腊),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把版图扩张到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强盛帝国。帝国存续期间,西亚各地的奴隶制文化经济化得到进一步发展。波斯文化使用楔形文字,造型艺术有较高的成就,如著名的波斯波利斯的百柱厅、浮雕和壁画等。公元前330年,波斯第一帝国被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所灭亡。
\r\r[2]阿胡拉·玛兹达:在古代伊朗宗教里,特别是在琐罗亚斯德教里被奉为最高的主神,是“唯一真正的造物主”(意为“智慧之主”)。阿胡拉·玛兹达在善恶二元论中代表光明的善神,与代表黑暗的恶神安哥拉·曼纽进行着长期的战斗,最后取得了胜利。古波斯经里认为全知全能的阿胡拉·玛兹达创造了宇宙,也创造了火,并维持着宇宙的秩序。阿胡拉·玛兹达为“无限光明”,能净化万物,用火来辨别正邪并将真理赐给信众。大流士一世时,琐罗亚斯德教成为波斯的国教,阿胡拉·玛兹达成为诸国王最伟大的保护神,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及以后的各代国王都崇拜他。后因印度和波斯的战争,阿胡拉·玛兹达被印度教吸收成为魔神,转入佛教之后又被称之为阿修罗。
\r\r[3]波塞波利斯:又被称为“波斯波利斯”“塔赫特贾姆希德”,意思是“波斯人之都”或“众神的王国”。是大流士一世,为了纪念阿契美尼德王国历代的国王而下令建造的第五座都城,位于伊朗扎格罗斯山区的一盆地中,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第二个都城。其遗址发现于设拉子东北52公里,主要遗迹有大流士王的“觐见大厅”“薛西斯宫”“万国门”与“百柱宫”等。历经大流士一世、薛西斯一世及阿尔薛西斯一世三个朝代,前后共用了60年的时间得以完成,存储了波斯帝国大量的珍宝财富,被形容为太阳底下最富有的城市,是波斯帝国鼎盛时期最繁荣的象征。
\r\r[4]阿萨栖兹王朝:又名帕提亚王国或安息帝国,伊朗古代历史中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奴隶制国家,阿萨栖兹一世为王朝第一位国王。随着塞琉古帝国的衰弱而开始四处扩张,全盛时期的阿萨栖兹王朝,疆域北达小亚细亚东南的幼发拉底河,东抵阿姆河。与汉朝、罗马、贵霜帝国并列为当时亚欧四大强国之一。由于位处罗马帝国与汉朝中国之间的丝绸之路上,成为了商贸必经之路,它与古代中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阿萨栖兹王朝是由不同文化的民族组成的国家,它吸纳了包括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及其他地区文化的艺术、建筑、宗教信仰及皇室标记。但后被波斯的萨珊王朝所取代。
\r\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