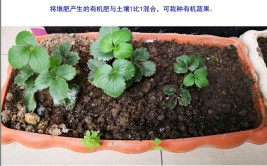稍稍留心便会发现,这些茅亭的屋顶顶着厚厚的青苔,下面覆盖的不是瓦片,而是树皮铺设的。这些散落在密林流水之间的茅亭,更像是大自然的手笔。原木为柱,枯藤为挂,树皮为瓦盖,老根为凳,雨天不漏,炎日无暑,与清幽山景浑然一体。这如影随形的背后,是能工巧匠的遗风、更是历代匠人精心守护的结果。
无独有偶,日本的千年之美——京都御所的屋顶也是用树皮铺设的。这种古老的建筑手法,在中日两国历经千年延续至今,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与风情?
独有茅亭

树皮为瓦 老根为凳
进山门数百步处,一间精致的二层茅亭,侧立于清溪之畔。这便是青城山有名的“雨亭”,也是山上唯一的两层茅亭。亭名是根据青城山多变的气候特点命名的。相传唐上元二年(761年)秋,客居成都草堂的杜甫游青城,刚进门便遇雨骤发,杜甫便在山道边古楠下避雨。后来,此处便修起了供游人休息避雨的茅亭。亭联是王维的《山中》:山路原(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与青城山本身的“幽”不谋而合。
作为中国道教四大名山之一,青城山的古建筑、古遗址、历史传说、饮食风俗,林木花草,无不蕴含着浓厚的道教文化,散落在各地“茅亭”作为其中之一,当然也不例外。
道家崇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法则,而这茅亭的屋顶,便由山前的一层树皮顶,到山门口的两层树皮顶,再往里走的茅亭就是三层树皮顶,在层数上充分体现道家思想。既能引导人们休憩观景,本身也和环境融为一体,正所谓“唯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亭得天全”。
青城山的亭子,独特在其以不去树皮的原木为梁柱,枯藤为挂落,树皮为瓦盖,老根为凳;卯榫结构连接,雨天不漏,炎日无暑, 清幽山景浑然一体;不拘一格,随影赋形,深深寓意了道教道法自然的思想。
“这里的亭子有三面、五面、六面的,共126个茅亭。都很典雅漂亮,盖一个亭子,从立柱到盖亭,差不多需要20多天。”刘崇贵,都江堰市青城山镇青景村的本地人,在青城山景区修葺茅亭已有10多年。因为长期巡山,皮肤被晒得黝黑,长期攀爬,人显得精瘦。一件略显宽大的军绿色外套,因为爬上爬下,已有些脏。
这一天,他正好要给雨亭重新搭树皮顶。
修亭匠人
精选深山针杉树皮铺顶
一个背带磨得光亮的竹制背篓,装着准备好的树皮、镰刀、竹竿、自制钻孔工具等,放置在雨亭石阶下,修葺茅亭的工作,即将铺展开来。
刘崇贵话不多,动作麻利。竹竿被斜立起来,镰刀飞快地剖下,即成两半长竹片,将要用来夹树皮。
长约1米5的一对竹片,一头搭在刘崇贵身前的石头平面上,一头搭在差不多高度的石阶上,中间留出40公分的间距,像一副担架,要摊住树皮。
刘崇贵整理树皮。
深棕色的树皮,还带着森林气息,开始从背篼里面苏醒。刘崇贵的一双大手粗糙,但铺起树皮来却柔软至极,一一抚平整。
“这是在做滑竿吗?”正值下午4点过,不断有下山的游客路过。对于外地游客来说,这番造型,果然有点像刚刚才新鲜体验过的滑竿呢。
“这个树皮哪里来的呀?”、“这是什么树啊?”游客们的问题接连不断。
“树皮是从阿坝州林场那边采买的针杉树皮。” 刘崇贵手上活不停。
“选针杉有啥讲究啊?”游客好奇地追问。
“因为它耙和,遇上下雨不得漏。如果没有遇到强风、树枝掉落砸坏这类的自然灾害,一个亭子基本上十年之内都不用维修。”刘崇贵解释道。
除了天灾,还有动物的骚扰,祸首就是青城山上随处可见的松鼠。“松鼠跟猫儿一样,喜欢打磨自己锋利的爪子,它们除了在树干上磨,还喜欢在亭子顶上磨,磨烂了就得换树皮。”说到这里,刘崇贵边笑边摇头。
身手矫健
“嗖嗖”两下爬上亭檐
结结实实把树皮错落铺了三层后,刘崇贵又在树皮上下两端加了一对竹片,初步固定。“对了,现在开始把树皮打洞‘缝’起来。”用啥缝呢?众人好奇。
刘崇贵神秘地笑了,展示了“缝线”:竟然是刚才用剩的篾条。
刚准备动手,他又摇了摇头,“这些竹篾不能用了,有点干了,没韧性。”刘崇贵边说,径直向山上走去。
有些湿滑的山路,老刘如履平地。往上爬了一小段,便找到了新鲜的竹子,利索地处理干净枝叶,“就是要这种新的才可以,这种竹竿生,韧性够、也柔软。”
既然要“缝线”,那就得有针。这针,是老刘自制的。一个简易的木头手柄,正中连着一根铁钉,足以在树皮上打孔。一手固定树皮,一手左右转动,就打上了孔洞。为了灵活操作,老刘从不戴手套,手上也是伤痕不断。
将粗细合适的篾条穿过孔洞,重复绕两遍,再收紧作结,将结头死死压在竹片中,便能固定住树皮,又有适当的缝隙,可以承受雨点的重量。
“由于以前没有钢丝,古人就用韧性极好的毛条作为穿插工具,管得久,又方便。” 如此精妙的设计,在刘崇贵眼中,并不稀奇。
树皮顶制作好了,还需要搭到亭上去。没有梯子,怎么搭?“嗖嗖”两下,他已沿着亭柱和树藤,爬上了亭檐,再翻到茂亭顶上。一声招呼,下面的人帮忙将做好的树皮递上去,再进行固定就完成了。
刘崇贵翻下亭来,还神秘地补充:“平时他们喊我‘猴子’。”一句再正经不过的话语,却逗得大家大笑。
谁能想像,这样矫健的身手,已是一位51岁之人。
匠人团队
7个师傅 管126个茅亭
半个小时的劳作,雨亭修葺一新。重新立在亭外,看着阳光通过树缝散落在亭檐上,像金沙一般,那些用树皮作的屋顶,就像树皮原先保护树干一样保护着这个亭。
刘崇贵坐在了亭内,稍微休息,说起了一个团队的师傅们。“目前有7个固定的师傅,年龄大多在40岁至60岁。工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枯燥,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愿意学的。”10多年前,刘崇贵还是滑竿师傅,通过自己观摩学习,逐渐掌握了修葺茅亭之法。
每天早上,他骑着摩托车,在8点之前准时进山门,开始一天的工作。中午就吃早上从家里带来放在保温桶里的饭菜。
“我们一般都是沿着山路,查看有没有掉落的树枝,或者其他影响游客行走的阻碍,并一个一个地检查这些茅亭,有没有松滑、不牢固的情况,这126个茅亭都是我们负责维修检查的。”刘崇贵自豪地说。
不谋而合
日本京都工匠 用竹钉和桧树皮修葺皇居屋顶
明治天皇在移居东京后,曾因怀念京都御所而吟歌:“望东山 明月升 思故乡 清凉所”,而这座京都御所,作为日本传承千年的古建筑--千年之美,是以桧树皮铺成的桧皮葺为屋顶,有别于青城山的道教意韵,其追求的是桧树皮通过重叠所形成的曲线美。
树皮从采集到修葺完成,都需要工匠独特的工作技能和浩大的工程量。收集桧树皮,是在京都北部严寒的深山里展开的,爬到20米高的巨大桧树上的工匠,是日本国内仅存的20位取桧树皮的专业工匠,这种职业被称为原皮师。
他们为寻求优质的桧树而踏遍全国,仅靠一根绳子把自己绑在树干上,相当危险。而使用树皮刮刀的工种,则很好地体现了古人保护森林的智慧(桧树皮分外部的外树皮和里部的内树皮,而刮刀可以很完整地刮取外树皮,从而不伤害内树皮,不影响树木的生长)。
修理茅亭的工具。
树皮采好之后,要修葺工匠爬上屋顶进行修葺。工匠们横向排成一行,熟练迅速地把桧树皮一块一块地铺上,为了形成这独特的曲线美,桧树皮之间的间隔一定要是1.22厘米,不能有丝毫的偏差,钉上桧树皮时所用的是竹制钉子,因为左手要固定桧树皮,只剩右手钉,所以每个工匠将30根竹钉含在嘴里,然后一根根地取出使用,要修葺好一坪大的屋顶,大约需要1800根竹钉,工作量可想而知。
修好的屋顶,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华丽又带着几分自然,那流动的曲线美在这时也得到了最大的展现。
不管是青城山原汁原味的树皮顶,还是京都御所追求曲线美的树皮顶,因为其特殊的材料,修葺好的屋顶每过一段时间,都需要重新修葺一遍。正是工匠们独特精湛的技术和历代的传承,使得这些美轮美奂、绘制精巧的建筑得以保存至今。
在追寻美和意韵的同时,大家也都注意到了对生态的保护,日本的原皮师,采用了树皮刮刀的工种,只剥桧树的外树皮,保留内树皮,使其可以正常生长,而青城山除了取材不伤害树木外,犹如原生建筑般的设计手法和建造技术,就是对自然的回归。
封面 赖芳杰 实习生 武明 摄影 何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