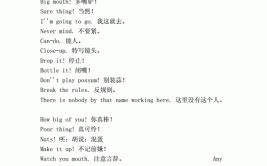村里的孩子极少,就五六个而已,要么还在牙牙学语,要么已经长成了少年,就我一个五岁女娃独独立在中间,总不能跟他们合群,所以那时我最常做的一件事和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坐在村口那棵不知道怎么倒了的大柏树上,眺望着唯一的那条可以走出这穷乡僻壤的泥路,盼望着我的父亲母亲能从那遥远的北城里快点打工归来。
偶尔我也会瞧瞧那绿油油的稻田,望望村庄里寥寥可数的几间破旧土房,从村口看到村尾。
我看得最多的便是狗爷的家。

狗爷的家坐落在村口的路边,我坐的大柏树的对面,我只需要抬头向对面一看,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至于为什么要抬头,是因为狗爷修房子时,在地面垒了个土坡,把房子修在了土坡之上,到底有着个什么寓意,我虽曾听老辈们说过,可现时却已经记不清了。
只是记得那时我看着狗爷的房子,常常都会羡慕,想着自己也住在这儿就好了,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但也常常替狗爷担心,这松松垮垮的土坡,遇上大雨就不怕滑坡塌陷吗?
可结果也是怪哉,无论是多大的风,多大的雨,我担心的事情一直都没有发生,狗爷房子下土坡的土一直到很多年后搬迁时都没有松落一捧。
却好像一直都在变,变了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时间长了,我看得多了,加上年龄大了些,我就再也喜欢不上狗爷的家了,甚至心中还生出了些许厌恶感,往日的担心也不复存在,我还老是小没良心的诅咒他的房子快点塌陷。
因为狗爷是个四十多岁的光棍,更无儿无女,好似以前干着伐木的行当。现只能靠着捡破烂,农忙时给各家帮帮忙,挣点小钱勉强过活。他家的房子自然最破,最小,看起来最邋遢,地面也是坑坑洼洼,到处都是胡乱堆着的破烂,地上的鸡屎,也不知道打扫。
平时还好,影响不了大家的正常生活,可到了夏天就糟糕透了,鸡屎和他捡的破烂发出的味儿交错在一起,臭得都可以把人的眼泪熏出来。
他的邻居,肖妈妈还有许婆婆不知道站在他家门口叉着腰骂了多少回了,可狗爷还是从不知道收拾。
我也渐渐的不再去村头。
每次遇见狗爷,我更是夸张的绕得多远,一是因为他身上的味儿我着实受不了;二是因为他不善言谈,还老是板着脸,像极了电视里演的那种坏人。
再到大约我快七岁的时候,狗爷不知从哪儿捡来了个女人。没人知道她从哪儿来的,也没人知道狗爷把她怎么带回来的,更没有人来这儿寻过这个女人。
乡里的人哪里懂得把她带去公安局?就算懂得,那人也是狗爷带回来的,我们想管也管不了。
最终的结果是:女人跟狗爷生活在了一起,得了个名字,叫“羊子”。这名字是狗爷取的,为什么取得这么不土不洋,这就要问狗爷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羊子是个哑巴,因为她从未与我们说过话,她只会拿一片破瓦在墙上刻画或拿一根短短的树枝在地上写着什么。
你就那样看着她,她就跟你笑笑,笑熟了过后,我试着问她:“羊子,你吃了饭没有?”
羊子点点头,有些羞涩的回答道:“嗯,吃了。”
原来她不是个哑巴。
可是后来的有一年,狗爷家的猪死了,那时候的一只猪是何其的管钱啊。
他就在村边把羊子捆在树上,一直说:“就是这个傻婆娘把老子的猪给喂死了喏,该打!
”
然后那扁担一下一下的落在羊子的身上,任凭羊子怎样的哀嚎,他都没有停下,当时要不是几个平时就很热心的老妈子把狗爷拦下,羊子可能就会被狗爷打死吧。
我不知道猪究竟是不是羊子喂死的,我想狗爷也不知道,羊子更不知道。
我只知道,后来羊子好像真的变成了哑巴,也变得越来越痴傻疯癫,她没日没夜的就在田坎边时而哭时而笑,时而张牙舞爪……
她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好多年,直到老家的房子拆迁,羊子不见了。有人说狗爷把羊子扔了;有人说羊子的家人来把羊子接回家了;还有人说狗爷是贫困户,吃的是低保,羊子被国家安排到了县里的精神病院。
因为拆迁过后我们一家就去了街上,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狗爷和羊子也在随着时间被我慢慢淡忘。
再次想起他们的时候,是在2019年的暑假,我与奶奶在街上喝茶,一个人风风火火的边跑边吼着说:“你们快去看,德财倒了,倒在了前边的路上,人已经来不起了!
”
当时我出于好奇问了一句:“这德财是哪家人啊?”
奶奶告诉我说德财是狗爷的名字。
哦,原来狗爷叫德财,在他死前我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