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我2、3岁的时候,跟妈妈到姥爷家,记得姥爷住在东间,见我和妈妈来姥爷很高兴,妈妈和姥爷说了几句话就不知去忙什么了,这时姥爷起身到台子上(就是炕和正间锅灶之间的墙壁处留出的半凸字的平台)拿下一“石头盒子”(用红高粱杆皮编制的,后来才知道一般老人都是把好吃的点心之类的东西放在其中),从盒子里拿一个型似“海绵的轱轮车”的东西给我,我赶紧告诉在正间的妈妈,“妈妈,俺姥爷给我一个海绵轱轮车!
”妈妈说,那是蛋糕快吃了吧!
”原来这个不是海绵轱轮车是好吃的蛋糕!
又香又甜!
是我长到那么大吃的最好吃的东西!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认识蛋糕,也是第一次吃蛋糕。
随着条件的逐步改善,一年也能吃两次蛋糕或黑桃酥,一般都是大舅从北京或姨从青岛回来带的,很少有其它出门人回家送的。
当然,大舅从北京回来还有糖果吃,那时候确实很馋,不管是点心还是糖果,吃在嘴里总想把那香甜的感觉留住,但好像肚子也是迫不及待的召唤——下咽!
这样一块糖果或糕点总是很快被吃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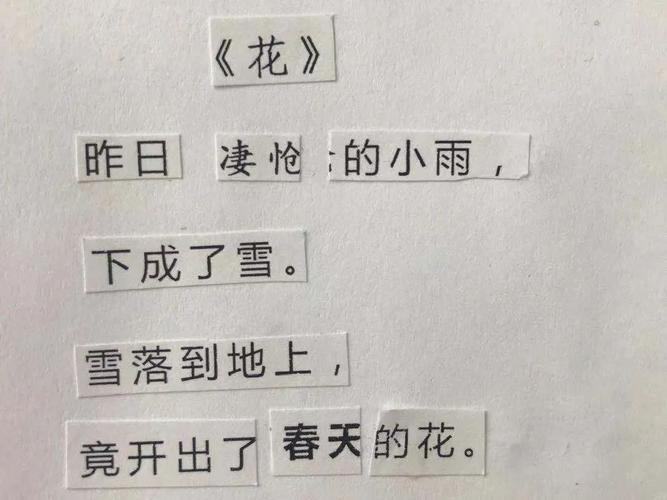
说起糖果又想起了另一件事:
记得那一年春节前,盼望已久的大舅从北京回来到我家老房子(那时是租人家的房子),和我爸妈在家说话(在东间屋),我们兄弟姐妹也喜欢围着大舅,大舅和我爸妈谈了家里的正事,我们在叽叽喳喳肯定影响他们说话,房间又小。本来每个人都分了糖果了,大舅又给我们一个人一把糖果让我们去外边玩去,包括我的一个小伙伴亚成,也得到了一把糖果。这样我和亚成兜揣都去街上玩了。玩了一会儿,只见我们村的“良”(大我4、5岁)从西朝着我们俩这走过来,碰上同村的小伙伴,跟人家要糖吃(当时临近春节,一般小孩兜里都有几块糖果,平时一般是没有的)人家说没有,他不信就去翻人家的兜。我看到也听到了,这时躲起来不妥,不躲起来白白的给他糖又舍不得,如果撒谎说没有,他再翻我的兜可能失去的糖更多,因为我兜里确实有不少糖。我急中生智!
把兜里都糖藏起来,他再要就说没有糖,这样既不能得罪他,又不能损失一块糖。随即跑到我家麦秸垛迅速掏出兜里所有的糖藏到麦秸垛秃噜下来的麦秸下面。而后回到原地,亚成还在那,那个“良”已经离去,问了一下亚成,他被良“抢去了”好几块糖!
我庆幸自己躲过一劫!
随后,又去取藏在麦秸下面的糖果,掀开麦秸把糖果再一次的装到兜里,因为当时情况紧急,没有数一共藏了多少块糖,总是担心有遗漏,所以就扩大范围寻找,把麦秸掀起更多,这一掀看到一个黑皮包!
当时既紧张
害怕又有惊喜不已,因为有些什么定时炸弹的谣传。不管那么多提着皮包跑回家告诉了爸妈。这时大舅已不在我们家了,天下起了鹅毛大雪,夜幕降临。
我爸拉开皮包看了一下,里边有人民币100多元(当时的100我估计相当于现在的1万,可能是1974、5年或1973、4的事),还有些吃的糕点和用的东西。后来把这个皮包交到黄山边防派出所。派出所找到了二村在青岛工作的失主。失主夫妇带着东西登门致谢!
派出所反馈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二村那夫妻两个搭便车从青岛回老家二村过年,带的东西不少,忙乱中被他们同村的“小明”给顺走了一个皮包,藏到我藏糖的地方。捡到皮包的第二天早晨我去捡皮包的地方看了一下,雪地里留下了还没被完全覆盖的脚印。小明是个惯偷,在派出所是挂号的,为此派出所把他抓去,他也招供了。




